欢迎来到格策美文网
写作《前赤壁赋的中心思想》小技巧请记住这五点。(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3 0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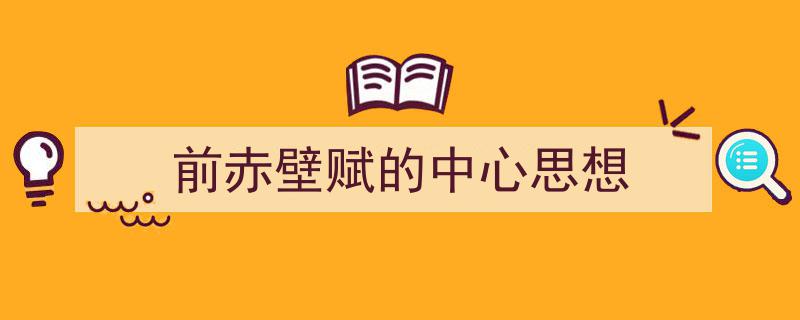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在撰写关于《前赤壁赋》的中心思想作文时,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1. 理解作品背景:《前赤壁赋》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赋文,描写了作者在赤壁之战遗址的游览体验。在写作时,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经历。
2. 分析文章结构:了解《前赤壁赋》的结构特点,如开头、正文、结尾等部分的内容安排。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3. 重视主题思想:在分析《前赤壁赋》的中心思想时,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a. 赤壁之战的历史意义:通过描写赤壁之战,表达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 b. 人生哲理:从游览赤壁之战遗址的经历中,提炼出对人生、处世、道德等方面的思考。 c. 文学艺术特色:分析苏轼在赋文中运用到的文学手法,如对比、象征、夸张等,以及这些手法对表达中心思想的作用。
4. 分析人物形象:在文章中,苏轼通过描写赤壁之战遗址、自然风光和人物对话,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形象。在写作时,要关注这些人物形象对中心思想的影响。
5. 结合现实意义:在阐述《前赤壁赋》的中心思想时,要关注其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 借鉴历史经验,启示当代人
陈立今老师:《前赤壁赋》典故意蕴浅析
《前赤壁赋》使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经典文章,但对于其中典故你又有多少了解呢?来和小喵一起看看陈立今老师的讲解吧~
《前赤壁赋》典故意蕴浅析
文 / 陈立今
《前赤壁赋》文采如三秋明月,情韵深致,理意透辟。该文的可圈可点之处太多了,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典故的巧妙而准确的使用。全文引典十余处,这些典故的使用建立在民族共通的文化情理感知基础上,且多能化典无痕——这得益于苏子深厚的文学文化功底——故后人读之诵之,于精短的文字中能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脉搏,能随着作者的情感起伏而产生心灵的悸动。但由于时代原因,对于当代中学生来说,仓促间对不少典故的意蕴还难于领会,为帮助学生学习,现将这些典故罗列并简要分析如下:
1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典出《诗经·陈风·月出》,此句是互文的修辞手法,意即诵歌“明月”这首诗中“窈窕”这一章节。这一章节的内容是:“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实际是单相思的诗句,看见了佼人(即美人)身影容颜了,但是得不到,于是心里就颇不宁静了。而“楚辞”又有以美人比君主之例,再联系后面扣舷而歌的“望美人兮天一方”,这实际上就证明了苏轼游赤壁时是带着浓浓的儒家事功情怀的,他并没有见明月而超脱,反倒由明月而起兴,想到了“窈窕”的美人——尽管现实中的美人神宗皇帝赵顼似乎并不窈窕。
苏轼书《前赤壁赋》(局部)
2 月出于东山之上
关于此句,见解纷纭。有人以为是典故,有人以为非典。持用典者认为出自鲍照《朗月歌》,全诗如下:“朗月出东山,照我绮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靓妆坐帷里,当户弄清弦。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先。为君歌一曲,当作《朗月篇》。酒至颜自解,声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后人揣测鲍照的“佳人”定有所喻,但以今人的理解习惯看,此美人就是个实实在在的美人,就是使人觉得“千金何所重”的美人,未必有什么寄托。我倒觉得非说典故的话,到可能出在《诗经·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朱熹释云:“东山,所征之地也。”也就是说代指远征、远谪之地。这与苏轼的处地倒是相配。
3 纵一苇之所如
很多人认为此典出自《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但权威孔颖达解释说:“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面渡,若桴筏然,非一根也。”这样一来,苏子泛舟的轻盈感就没了。所以我以为此典出自佛教经典“一苇以航”比较妥帖,这个典故也称“苇叶渡江”。相传菩提达摩遵照其师般若多罗的懿旨来到中国传法,梁普通八年,被笃信佛教的武帝萧衍迎来首都建康。武帝一见到菩提达摩便问:“朕度人造寺,写经造像,能折合多少功德?” 达摩答道:“没什么功德。”武帝又问:“为啥呢?”达摩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都是些有为之事,而非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解,与达摩“语多不契”,达摩飘然北去,武帝忽有觉悟,深感懊悔,马上派人骑骡追赶。追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一行人被夹在两峰之间。达摩正走到江边,看见有人赶来,就在江边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踏叶渡江而去。达摩没有给梁武帝觉悟改过的机会。苏轼“纵一苇之所如”的潜意识中有一种道家的超脱,皇家不用我,我还不伺候了,山水动人,你再别找我。只不过这个超脱在苏轼文中与生活中并没有一以贯之。
4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前者典出《庄子·逍遥游》:“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后者典出《楚辞·橘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苏世”意为从世道中彻底苏醒。有人评价说苏轼同时想到这两个典故,似乎是片刻间入了道家,其实不然,列子御风是有所待的,道家超脱而不标榜,道家讲求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绝不追求独立的味道。“御风”要有凭借,“独立”失之标榜,这两个典故连用,恰恰是苏轼内心“颇不宁静”的体现,内心期盼事功与期盼自我解放的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5 桂棹兮兰桨、望美人兮天一方
此两个典故均典出《楚辞》。前者出自《楚辞·湘君》:“桂櫂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是 “用桂树做长桨啊木兰作短楫,击破坚冰啊堆积似雪。摘取薜荔啊去往水中央,采撷荷花啊在枝梢。两心不相同啊有了媒人也徒劳,相爱不深啊感情说断就能断。”这是以一位女性湘夫人的视角表达对男性湘君的渴盼。湘夫人是“斲冰兮积雪”,苏轼是“击空明兮溯流光”,前者“冰”硬,后者“水”软,所以苏子“老不生事”,终非屈子。故苏子能“九死南荒吾不恨”,屈子则做“怀沙”之赋,自沉汨罗。后者出自《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这是以男性大司命的视角对女性少司命的呼唤。不管是以男性还是以女性身份呼唤,苏子终究没有寻到自己的“美人”,“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湘君湘夫人图》(局部)
6 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前者典出李贺《李凭箜篌引》:“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文中要描写萧声“呜呜然”,“老鱼跳波瘦蛟舞”描写的是箜篌之声,同时乐音,这是相同之处,但还是浅层的,深层的是作者李贺的短命,这直接导出后面人生短暂的感慨。后者典出白居易《琵琶行》:“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自己的命运和琵琶女有相通之处,此刻都独守空船,这也只是浅层次的,深层的是自己的命运和《琵琶行》作者白居易的命运也很相似,都是40余岁被轰出朝廷,微官青衫。
7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典出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应是苏轼当时所见;“乌鹊南飞”,当时也真可能有只黑鸟飞过。但还要联想《短歌行》的主旨,紧接的语句是“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自己就是无枝可依的乌鹊。再接下去“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作者是多么希望有一个能为自己一饭之间三吐哺的君主呀。
8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典出赤壁之战。此地山川,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周郎曾大败曹军,建功立业,尤其是周瑜赤壁之战时年仅33岁,35岁就完成一世功业,“长天曲就宴周郎了”。这对作者刺激很大,因为作者47岁还在团练副使的地位上熬着,这对从小立志要做范滂的苏轼来讲,大有“青袍今已误儒生”之痛。注意这里的孟德、周郎并没有后世通常的褒贬意义,而是慨叹人生不永,功业难求,“是非成败转头空”。
9 逝者如斯
典出《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但苏轼这里其实并未用孔子愿意,苏轼后半句不是“不舍昼夜”,而是“未尝往也”,有教学分析说这是片面夸大静止,以求得对岁月将晚的慰藉。其实不妥,苏轼在这里强调的是事物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前水非后水”,但“古今相续流”,联系下文“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也可推知这层意思。苏轼其实并不是靠夸大相对静止来宽慰自己,而是用近似现代科学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之类来宽慰自己。
10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评论家认为此四句一句一典,固然有道理。但其实对中学生而言不必搞得如此繁琐。余以为此句主要典出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句。《与韩荆州书》是京教版高中语文重要篇章,李白到襄阳——荆州长史驻节襄阳,上书长使韩朝宗,希望能经过韩荆州“品题”,拿个推荐信,走捷径,成“佳士”,但终无成果,借助酒力,愤而做《襄阳歌》:做官干啥,俸禄啥用,老子醉游山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我不使人间造孽钱。但这个”不使人间造孽钱”,不是唐伯虎的“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倒很有几分郭德纲“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的意境——仔细琢磨,肯定是这样。
如果细推敲,文中还有不少典故,如“余音袅袅”“无尽藏”等,但把一篇美文解读得处处皆典,绝非笔者本意,故适可而止。但单一文本的价值意义往往要借助其他文本方能产生“增殖”。
作者简介
陈立今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兼任北京市西城区高中语文教研员,北京普通教育名师研究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文言诗文和写作教学方面有独到见解。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刘桐
专栏画家:黄亭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说《前赤壁赋》是宋代文章中的压卷之作?
赵孟頫所绘苏东坡像。
苏轼文集有赋一卷,《前赤壁赋》无疑是其中的最佳之作。苏轼文凡七十三卷、两千余篇,其中亦未有胜过《前赤壁赋》的。甚至不妨说,在三百六十册、八千多卷、十六万多页的《全宋文》中,《前赤壁赋》亦为其中的最佳而可以称为压卷之作的一篇。苏轼的老师欧阳修,赞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见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模仿一下这个句式,我们就可以说:“宋无文章,唯苏轼《前赤壁赋》一篇而已。”这当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此赋的佳处何在呢?这却不易作答了。譬如有人食指大动,饱食一顿大餐,你要问他好吃与否,那他是可以不假思索,立即便能说出的,但若要问好在何处,却不一定说得清楚了。而妙于语言的黄山谷在形容茶的味道时,也就只能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见《品令·茶词》)——这真是等于没说!但我还是要饶舌一番,“尝试论之”。《前赤壁赋》的好处,也许可以这样说:主要是在写景、抒情和说理三者高度的融而为一,并且笔补造化造了一个高妙澄明之境,它不仅文辞工,抒写妙,有苏轼本人所说的行云流水之致,而且在精神上有相当的深度,它对于人生的根本的问题作了极简隽的探讨,而深具哲学之意味。以前人说《庄子》是“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前赤壁赋》虽不是“文学的哲学”,但说它是“哲学的文学”,是决无可疑的。
湖北省黄冈市东坡赤壁的《前赤壁赋》。 (人民视觉/图)
它从眼前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来谈万物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勃窣理窟”,而富于辩证的意味。“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几句的句法,是本于《庄子·德充符》的:“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其思想,则本于僧肇《物不迁论》的“四不迁”之说: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见中华书局本《肇论校释》,17页)
僧肇就是肇法师,是鸠摩罗什的最杰出弟子,号为“解空第一”。肇法师的意思,是说山风旋吹是静的,江河流水也不曾流,野马是天地间的游气,它虽飘动而实不动,就是日月在天流转,也不是真的流转。这就是所谓的“四不迁”。这是《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及一百三十所提过的(“东坡之说,便是肇法师‘四不迁’之说也”)。《物不迁论》中又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肇论校释》15-17页)
肇师的这一节论证,姑不论其对错,其阐说之妙,却是首先必须要承认的。为了说得清楚些,我且把肇师说的“往物”“今物”“昔物”,换成梁启超的名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那么肇师的意思,就差不多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并不是同一个我。昨日之我,可以于昨日找到,但在今日就无以觅见了,因为在今日的乃是今日之我,而非昨日之我。亦以此故,昨日之我,也就并没有从昨日到今日来,今日之我既非从昨日来,则今日之我,亦必不往明日去。所以每一日中,都各有一我,如电影的胶片上,每一格都各有一人,而各各不同,而各格之中的各各不同之人,亦必不互为往通,不互为往通,那当然就是静而非动的了。看电影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虽然胶片本是静的人物,但一经放映,却又是实在是动着的。但那是一个假象。肇师的想法,也与此仿佛。
与肇师说相似的,是古希腊的芝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引了芝诺的说法:“如果每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本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移动位置的东西在任何一个霎间总是占据着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飞着的箭就是不动的了。”(据《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34页;娄布丛书本《物理学》英译则作“Zeno's contention that ‘the flying arrow is not moving’ depend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time of its flight is made up of inpisible instants in each of which it is at rest”,这就是西方著名的“飞矢不动”说。芝诺主要是从空间着想的,肇师则是从时间,所从想之途不同,而所归则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诚然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一派与惠施互辩的,另有一说:“飞鸟之景(按即影字),未尝动也。”影子是无光处,它是无,就好比拓本的不着墨处,因无而为字。飞鸟是移动的,而飞鸟之影却不动,但这是易于理解的。《墨经下》:“景不徙,说在改为。”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云云,是其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三册1536页)也就是说,鸟影是光为鸟蔽而有的,鸟移,后影已非前影,影既非一,则无从言其动了。这是与芝诺之说,有本质之不同的。
《庄子》中真为肇师所用的,是《田子方》中仲尼答颜渊的一节。颜渊问仲尼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仲尼为了破颜渊的惑,便对他说道:
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中华书局本《庄子集释》,707-709页)
这就是《物不迁论》的“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之所本,其详如此。《田子方》中的这一大段,是《庄子》中的最上等的文字,也是我最喜欢读的文字之一。它的大意,是说人随大化而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而每时每刻之我,也就与前我不同,所以一交臂之间,故吾已尽失。这真是通达了大道,而揭出人生的真相。肇师正是借了此事,来证他的“四不迁”之说。而苏轼则是用肇师的说法,破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外羡的妄念,所以哀、所以羡,也正是为了我执之故,所以说“而又何羡乎”,人生于世,又有什么要羡的呢。其实,人生的烦恼,也就起于这个对外的羡,以及在内的我执。苏轼就是要破除这个执和羡,而提出他的与外物“共适”的主张。这就是: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按,“适”字别本作“食”,非是。参观予《赤壁赋之适字》,见2019年8月1日《上海书评》)
“共适”的“适”,就是融洽地在一起、彼此适合、彼此悦适,各得其所。这个“适”的含义可说是极丰的,也是最值得玩味的。要做到“适”,就要抱一种欣赏的态度,而不可执著,而必须忘掉彼此、忘掉物与我。这里所说的“忘”,不是普通意义的读书、学知识因记忆力不佳而忘掉了,不是这个忘字,而是中国古人所体察出来的心与物之间的一种境界。《庄子·达生篇》云:
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集释》662页)
“屦”是鞋子,“要”就是“腰”。当你想不起、忘掉了你的脚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鞋是适你的脚的,你也就处在“适”中。你想不起、忘掉了你的腰的时候,那也就说明你的衣带是适你的腰的。而当你忘记了是非,那就是你的心在“适”中了。最后把“适”这件事也忘了,那就臻于最高的“忘适之适”之境了。鲁迅有一篇戏谑之文,题目很长,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但其中有几句,说得颇对:
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上海书店本《南腔北调集》,105-106页)
这正好是可以作庄子的话的注脚的。事实上,这一境界,也就是《庄子·大宗师》说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相忘”,鱼在水中不知水,人之沉潜于学问,亦若鱼之在水,得其乐而忘记了人世,那就是“相忘乎道术”了,那也就是孔子的“其为人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反之,王守仁《传习录》说的“持志如心痛”,则是要学者在用功之际,每时每刻,都不要忘掉所立的志。这五个字比喻得真好,因为心一痛,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必自然一齐集中在这个痛上了,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但这是进学修业的一种功夫,它只是初阶,不是学问的最高的境界。人生的一切烦恼,皆缘于不能忘,而执著于追求外在的事物,包括金钱、权力、地位、事业及不朽的声名,也包括生命,等等等等,对外物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抱着贪着、占有、据为己有之念,本来是可以没有烦恼的,但是一抱此念,人生的烦恼也就纷至沓来了。这是因为不能与外物“共适”,也就是执著、痴妄,而不能得“解脱月”。
王培军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