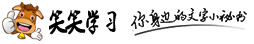欢迎来到格策美文网
格策美文教你学写《以第二人称的自我评价》小技巧(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23 10:14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以第二人称的自我评价作文时,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明确目的": - 在写作之前,明确你写这篇自我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自我反思、求职、申请奖学金还是其他原因?
2. "保持客观": - 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避免过于主观或情绪化的表达。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持你的评价。
3. "结构清晰": - 确保作文有清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 - 引言部分可以简要介绍自己,主体部分分点阐述自己的优点、缺点和成长经历,结论部分总结全文。
4. "使用第二人称": - 全文使用第二人称“你”,这样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 注意不要过度使用第二人称,以免显得不自然。
5. "突出优点": - 诚实地列出你的优点和成就,但要避免夸大或吹嘘。 - 结合具体事例或成就来证明你的优点。
6. "正视缺点": -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说明你正在如何努力改进。 - 避免用消极的语言描述缺点,而是用积极的态度表达改进的决心。
7. "展示成长": - 通过描述你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和成长,展示你的进步和成熟。 - 举例说明你在面对挑战时的应对
董达 陈巍:嵌入社会认知——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
摘要:人的社会认知的基本能力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是相连续的。这意味着第二人称交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单元本身即构成了界定该视角内涵的严格约束条件。对第二人称视角内涵的界定可以引入形式社会学中对两种最基本社会单元——二元体和三元体——的形式分析。在第一重含义中,第二人称视角被嵌入二元体中,第二人称关系即为纯粹的“我—你关系”,“我”的感知对象只是纯粹的“你”,“你”的感知对象也只是纯粹的“我”。在第二重含义中,第二人称视角被嵌入三元体中,原来的二元体中的双方直接受第二人称视角的引导同时注意第三方对象。
关键词:第二人称视角 社会认知 二元体 三元体 次级主体间性
作者董达,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副研究员;陈巍,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绍兴312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1期P72-P80
责任编辑:王志强
行为主义之后开启的认知革命号召回归心智主题,在历经两代认知科学的探索后,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者大致认同脑、身体和环境相互纠缠、相互依赖的系统性思维模式。心智和脑嵌入身体,而身体嵌入环境,对每一要素的认识均无法脱离与其他系统要素的关系。近年来,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和脑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更是巩固了此种脑—身体—环境相互纠缠和嵌入的观念。
在社会认知研究领域,主体间性或第二人称转向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并快速蔓延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教育学等科学实践领域。然而,以往对第二人称视角(second-person perspective)的研究可能并未真正基于社会结构的嵌入和构成来考察该视角在其中扮演的基础作用。具体而言,尽管当代的诸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第二人称视角对社会认知的重要意义,但是尚未明确主张第二人称交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单元本身即构成了界定该视角之内涵的严格约束条件。这一问题需要合并社会认知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两大领域的知识,以及可能需要承诺两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人的社会认知的基本能力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复杂性是相连续的;反过来说,社会网络的复杂性要求个体发展出可以使其去适应和处理该网络的足够复杂的社会认知能力。
本文对第二人称视角之内涵的界定引入了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中对两种最基本社会单元——二元体(dyad)和三元体(triad)——的形式分析。第二人称关系可能被更适当地称作“我—你关系”(I-you relation)。“我”在与“你”的交互中首要的感知对象只是纯粹的“你”,一个活生生的“人”(person);反过来说,因为该种交互的相互性(mutuality),“你”首要的感知对象也只是纯粹的“我”。对人的感知并非必然蕴含对在个人之上的超个人的社会单元的感知。这是在说,“我”在感知“你”的时候并没有先在地预设双方同处于一个二元体总体中。个体在存在论上实质性地嵌入一个总体与个体感知或认识到自身嵌入一个总体是两回事。对二元关系的交互性(interactivity)与总体性(totality)的分离是区分第二人称视角不同含义的关键。如果将第二人称交互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并锚定在人类个体发展早期,问题将聚焦于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是如何可能的。对该问题的解答一方面需要婴幼儿发展(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另一方面现在需要使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受到不同社会单元的必要约束。一个婴儿发展到一定阶段方能认识到与自己进行二元交互的另一方也具有其自身的心智,这取决于婴儿能够与对方共同注意二人之外的第三方对象。此时,婴儿感知到的对象不再纯粹是二元交互中的另一方,不过该对象最终是什么——根本取决于对方第二人称的有意向的指向。
一、嵌入:二元体和三元体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开辟的形式社会学中重点分析了两种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二元体和三元体。两种单元的区别首要地体现在构成成员的数量上,二元体由2个成员构成,三元体由3个成员构成。然而关于二元体和三元体的形式分析并不只是作为形式社会学体系建构的起点那么简单,因为齐美尔认为从二元体向三元体的转变实现了一个认识论的飞跃,成员数量大于等于3的多元体(polyads)中任意一个成员开始将超个人的社会单元作为社会认知的对象;此后,从三元体向四元体以至更多成员数量的多元体的转变均无法与前一情况的革命性进展相提并论,尽管两种转变从数量上看每次均只涉及一个成员的增加。齐美尔举了一个婚姻的例子:当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拥有一个孩子,此时构成一个三口之家,于是作为三元体的婚姻关系较之二元体的情况存在实质性转变。这一对夫妻之间的二元交互关系——无论是关于爱情、亲密、激情、合作还是背叛等——均因为现已属于一个更大的三元体而大为不同。进而,齐美尔称当这对夫妻拥有第二个孩子时,此时构成的四元体的转变较之成为三元体时的转变要小得多;第三个孩子的降生(构成五元体)导致的社会单元结构变化将更小,以此类推。所以,齐美尔形式社会学在数量问题上的要点是思考从二元体向三元体的流变究竟发生了什么。
成员数量大于等于3的多元体社会生活已经包含超个人的生活。在三元体中,任意一个成员退出,剩余的两位成员构成的二元体依然是社会化的。二元体是构成成员数量最少的社会单元,它较之其他多元体是最特殊的,因为这种单元纯粹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认知或人的感知(person perception)作为其心理学的感知基础。二元体中的社会交互可以说完全基于第二人称视角,因为任何一方所面对的只是另一方本身——而非去感知超个人的社会单元(即使是这个二元体本身)。从内在的观点看,人与人的关系应当被更准确地称为“我—你关系”。“我”对一个当下的、完整的“你”的直接感知就是“我”在这个交互二元体中社会认知的全部。这是在说,尽管“我—你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交互二元体,但是任何一方并不是在预设自身嵌入一个更高层级、更大总体的情况下去感知彼此;“我—你关系”中的社会认知或人的感知是在不考虑超个人的、“社会的”因素下进行认知和交互,因为他/她直接感知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三元体中的交互关系更为多样,一个成员所感知到的可能是其他两个成员构成的一个交互和同步的二元体。二元体中人的感知或第二人称互动与关于多元体的社会心理学是不同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特别区分了两者,并强调了前者在其工作中的基础地位:“讨论聚焦于人作为有待研究的基本单元……二人组及其属性作为一个超个人单元将不是关注的焦点。”总之,“人—人关系”或“我—你关系”并非需要先在地预设或者必然蕴含社会二元体(或多元体)的总体性。
在二元体中,任何一方的主动退出将导致社会单元的解体,姑且说留下了两个一元体(monad)。但是需要注意,在齐美尔的设想中,一元体并不是社会单元形式分析的起点。它似乎是任意一个成员脱离一个社会多元体之后暂时存在的潜在社会单元,以隔离和孤独的社会状态为标志。一个人的孤独状态同样是社会化的结果,即使这种社会化对社会交互的效应是负面的(以抑制和取消每一社会二元关系为目的)。一个所谓的“隔离的”自我依然存在于一个潜在的社会单元中;二元体要比一元体更根本,后者被预设先在地存在于前者中。如果考虑到齐美尔的过程观——一个“社会”可以被视为种种交互的过程,一元体要么是现实地非存在,要么只是暂时存在;它的最终稳定存在的现实状态依然属于一个多元体。
二元体—三元体流变不仅关涉社会实在层面上社会单元的本质问题,而且与人类个体社会认知早期发展的必要阶段转变有关。成年人所具有的在不同社会单元中进行社会交互的能力并非完全与生俱来,当然也并非完全是后天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些能力有着先天基础,也依赖婴幼儿期的基本社会交互练习。虽然已有一定的实证研究显示胚胎期的胎儿已经开始了与母体以及子宫外他者的交互迹象,但是考虑到彼时胎儿依然存在于非社会的子宫内环境,这里暂时将胚胎期的交互行为视为非社会的(或前社会的),将人类个体“社会”认知发展的正式起点设置为出生后。
社会认知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和认识能力,其发展存在一个必要而巨大的转折,尽管不同学者就这一转折的连续性存在分歧。简要来说,婴儿大致直到9个月才能发展出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能力,即他/她有能力追随另一个体共同注意同一个对象(人或物)。例如,一个婴幼儿顺着母亲手指指向的方向去看母亲正在注意的对象。两位观点对立的心理学家,科尔温·特热沃森(Colwyn Trevarthen)与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他们均承认联合注意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是两位赋予该现象的重要性以及背后的深层解释是非常不同的。简言之,特热沃森认为婴幼儿期的社会认知基本能力或他所谓的“主体间性”是相连续的,主要因联合注意现象的出现而分为初级主体间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和次级主体间性(secondary intersubjectivity)两个连续发展阶段。托马塞洛认为只有自联合注意现象出现,婴儿才开始将他者理解为有意向性的自主体(intentional agent),而像特热沃森一样向前追溯更原初的主体间性是不合理的,例如:“一些研究者,特别是特热沃森,相信这些早期互动是‘主体间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不可能是主体间的,直至婴儿将他人理解为体验主体——只有到了9个月时他们才能这么做。”不过托马塞洛承认特热沃森向前追溯的更原初的互动和交流也是社会性的,但是按其观点无助于从根本上促使“社会认知”核心部件的出现。
于本文而言,特热沃森—托马塞洛争论根本地涉及了二元体—三元体流变的问题。在发展的语境下,现在问题又增加了社会认知能力的维度。对9个月之前的婴儿而言,因为联合注意能力的缺失,他/她无法建立实质性的三元体社会交互关系。但是托马塞洛并没有否定人类个体自出生后一直具有基于第二人称视角与他人进行互动的能力。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主基调是“我—你关系”,但是这一关系自第9个月开始显示出多重性:首先,婴儿作为“我”一直具有与“你”进行第二人称互动的能力,但是在第一阶段只能将“你”作为对象(例如,母婴依恋);其次,在联合注意出现后,在第二阶段,婴儿可以与“你”同步地注意第三个对象(人或物),此时不再只将“你”作为唯一对象。这也即意味着第二人称视角可能具有多重含义。
二、第二人称视角社会交互首要地以第二人称视角为基础,部分地由婴儿社会认知发展的局限性所导致。第二人称视角具有相互性,这是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不具备的。“我”在感知“你”的同时也在被“你”感知。齐美尔在讨论视觉感官与二元交互的关系时已强调了这一性质,与陌生人的相遇可能是一个典型例子,例如:“在通过看以接受他者的同时,一个人也显露了自己;在主体试图了解其对象的同一行为中,他/她也向对象交出了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只用眼睛获取而不同时给予。眼睛向对方暴露了正尝试使对方暴露的灵魂。虽然这显然只在直接的目光接触中发生,但正是在这里,全部人类关系领域中最完备的相互性产生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均无此特点,前者内在地以自身为对象,后者把对相互性的取消视为观察之客观性的胜利。
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对人的感知存在非推理的直接性,隶属于一种基本的基于感知的朴素心理学(naïve psychology)。第一眼的相识(kennen)是基于推理的辨识(erkennen)无法替代的。辨识之可识别性来自以往的知识经验,以该陌生人个体与其他所有人共有的普遍属性为基础。我们可能推理说这个人是生龙活虎还是死气沉沉、是聪慧还是愚笨、是热情似火还是冷若冰霜,但是这些推理通过可分析的、可表述的个别属性分解了作为整体属性的“人”的第一眼相识。第一眼相识可以直接驱动交互行动,同时也是行动引导的;对人的感知的直接性和朴素性的强调可以矫正以往社会认知理论过于理智化的弊端。
社会认知中的交互论(interactionism)反对传统的理论论(theory theory)和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后两种理论在解释社会认知和社会交互中似乎显得主体或自主体过于“深思熟虑”和以自我为中心了,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基于以上讨论,无论是诉诸“理论”构建以推理他人心智的理论论,还是基于自我心智的模型去模仿他者的模拟论,实际上均是非即时相互的、非直接的(也因过于理智化而并不朴素)。当然交互论主张直接通达他心并未蕴含视角的互惠性(reciprocity of perspectives),后者已遭到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批评。当基于第二人称视角的互动被预设以两个视角之间的换位、融合或属于一个更大的总体性为目标时,交互论因被理智化而又蜕变成了一种传统的高级理论模式。关于交互论与传统的理论论、模拟论的关系,一种公允的说法或许是后两种理论是交互论的受限制的更高级的版本。在本文中,交互论与理论论—模拟论可能并不是敌对的关系,基于第二人称视角多重含义的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将两种进路理解为同一个框架的低阶和高阶部分(可结合以下给出的初级主体间性—次级主体间性理论)。
理论论和模拟论的另一问题可能在于对一方作为主体之优先性的预设;这是没有必要的,双方可以被认为是互为主体—客体的。一种更激进的观点认为“自我”来自第二人称交互。自我是什么,或者第一人称视角的来源,发展自基于第二人称视角的二元交互中对方的映射或确认。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指出婴儿在母亲的脸上寻找到了自我:“当婴儿看着母亲的脸的时候,他或她看到了什么?我认为在通常状况下,他或她看到的是自己。”
现在,通过引入二元体和三元体的形式社会学作为必要约束条件,第二人称视角至少具有两重含义,这两重含义均没有违反其交互性基本原则。如图1,A、B为“我”和“你”,两者之间存在第二人称实时交互。不过在左图中,A和B均以对方作为感知对象,A感知到的对象纯粹为B’,B感知到的对象纯粹为A’;两者之间的交互可以达到同步性(synchrony)的程度。在左图中,第三方对象C无法成为第二人称交互的对象,A或B均可以独立地注意C,但是并非在第二人称视角引导的条件下。在第一种情况中,婴儿可以注意到对方行为的变化,例如当母亲伸出一根手指,孩子的注意力立即转移到这根手指上;当母亲怀抱着一个玩具,孩子的注意力将转移到这个玩具上。第二种情况是与联合注意相适合的。此时母婴之间依然保持着第二人称实时交互,但是母亲与婴儿不再纯粹将对方视为感知的对象。当母亲指向第三方的一个对象时,婴儿认识到母亲正在注意那个对象,并且共同地注意这同一个东西。托马塞洛给出的解释是婴儿终于认识到母亲有意向地注意一个对象,于是将在自我之外的他者理解为是有心智的自主体。图1右中双向平行箭头代表着交互二元体的同步化。图1右之所以被区分为第二人称交互的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婴儿并不是通过其自身的第一人称视角自主地注意C,而是受第二人称交互另一方的直接影响而注意C。所以第二种情况依然以第二人称视角为基础。例如,婴儿与母亲一同看一本图画书,在图1右的情况下婴儿并不是自主地对看书感兴趣,而是直接受母亲二元交互的影响、愿意与母亲共同地注意同一本图画书。等到婴儿稍长一些,他/她在第二人称交互中不再总是被动的一方,开始主动注意第三方对象,而母亲则被引导着注意同一个对象(这依然与个体独立地注意一个对象的情况不同)。
历史上,尽管某些基于第二人称视角的哲学体系在哲学家那里已经得到较系统的阐述,例如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或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处,但是关于第二人称方法论的首次普及性的科学实践可以较明确地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婴儿发展心理学家对母婴二元互动行为的观察研究,这些先行者包括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特热沃森、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Tronick)等。在当时,他们使用至少2台摄像机同时分别拍摄母亲与其婴儿在同一场景中进行二元交互的胶片,然后在毫秒(例如,拍摄为1秒24格或16格胶片)的时间尺度上逐格分析双方的面部和肢体反应变化。结果显示母婴交互在非言语的层面上达到高度同步。这种毫秒级录像带分析技术被称为“微分析”(microanalysis)。结合眼动技术,研究者可以发现当母婴之间在前一秒发生凝视(gaze)时,婴儿的情感状态以及促进与母亲进行互动的自主调节行为在下一秒后变得更加积极。不过,关于母婴之间的高同步性倒不是说在整个时间段内的保持时间越长越好,例如这可能使得双方将注意资源全部分配到凝视对方上。特罗尼克指出,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同步性大致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内相匹配,在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则不匹配(mismatch),而这是一种常态;不过,健康的婴儿(相对于例如自闭症患者)具有良好的“修复”(repair)能力,能够在感知到二元交互不匹配时进行及时调节(例如,婴儿一旦发现母亲不理睬自己,会积极地发出声响或挥动手臂以引起母亲注意,以修复交互性)。
第二人称方法论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来自当代基于脑间同步性(interbrain synchrony)的超扫描(hyperscanning)技术。相对于微分析技术,实验者现在可以就双方的颅内认知活动一探究竟。实验中,进行第二人称交互的每一方被试均需佩戴测量帽,数据线连接着关于脑电、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或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等一系列技术设备。实验中所收集的数据来自真正实时的社会互动,具有高外部效度,这是以往基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脑科学研究无法比拟的。不过,超扫描技术可以应用于多人社会互动的实验研究,不唯独局限于“我—你关系”意义上的二元交互,例如,神经科学家现在可以研究一个大于3人的小型乐队或合唱团的脑间同步活动。
三、从初级主体间性到次级主体间性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在婴儿进入第9个月获得联合注意能力时同时存在。在这之前,交互的他者与视角中的感知对象是同一的,无法获得分离。无论如何,本文认为这两个阶段在第二人称视角的意味下应当被视为相连续的——但是蕴含多重性。托马塞洛所界定的“社会认知”的实质性含义对应了特热沃森次级主体间性以及之后的高阶阶段,而之前的关涉二元体内社会生活的初级主体间性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此外,交互论也以特热沃森二级主体间性作为其发展理论基础,但是在一般讨论中两种主体间性之间的多重性差异被忽视了,只是一味地坚持它们之间的连续性,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发展的转折何以会出现。
从形式社会学单元分析的视角看,这一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你关系”不可能仅凭自身存在,它从整体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隶属于一个总体,哪怕是关于这一二元关系的二元体。起初,婴儿被其照料者(母亲、保姆等)照顾,婴儿与其最亲近者之间的二元交互也是对方对婴儿的抚养;这一第二人称交互是暂时地脱离“社会”语境的,而在物质—能量的单向传递上是不可持续的(考虑现实生活中“啃老”的“巨婴”)。到了联合注意阶段,随着发展,婴儿在第二人称交互的引导下开始关注第三方对象。由此,婴儿开始过一种三元体社会生活。在第一重含义下,婴儿基于第二人称视角习得了交互性和同步性;在第二重含义下,婴儿则在第二人称交互的直接引导下习得了理解他人意图的能力,认识到二元关系中的对方是有意图的自主体。齐美尔看轻了成员数量大于等于3的多元体之间的流变,这似乎也符合这两种主要的社会认知早期发展理论的预设。
根据特热沃森的经典版本:在初级主体间性阶段,当婴儿与母亲进行面对面交互时,他/她对置于身边的第三方对象没有兴趣。当婴儿玩一个玩具时,他/她的注意力集中在玩具这一个对象上,母亲在一旁。不过需要注意,此时婴儿的行为(依照其依恋程度)依然受到与“人”的第二人称交互的直接引导,如果母亲不在身旁,婴儿将变得焦躁不安甚至哭闹。在次级主体间性阶段,婴儿在母亲第二人称交互引导下开始注意第三方对象。在一个拒绝的例子中,婴儿被母亲要求把手中的玩具给母亲,婴儿拒绝并躲避妈妈。这个例子与更小的婴儿被直接夺走玩具而哭闹是不同的;婴儿与母亲的联合注意对象是玩具,但是其行为受到第二人称交互的直接引导。一个“人—人—物”三元交互的理想情况:母亲向婴儿展示如何做一项游戏,婴儿接受并参与,双方在游戏中保持着匹配的同步关系。
图2中左图展示了“人—人—人”三元交互,右图展示了“人—人—物”三元交互。在左图中,如果不考虑作为总体性的三元体本身(ABC),被感知的对象可能有6个:A’、B’、C’、A’B’、B’C’、A’C’。这不是说A与B之间交互时可以感知到A’B’,而是C在与AB二元体进行交互时可感知到的超个人对象。图2右图与图1右图相同,均表示形成交互同步性的二元体对物C的感知,感知对象为C’。此时,A与B之间不再将对方作为唯一的感知对象,而是共同注意一个第三方对象。
以上讨论主要锚定于文章开头引入的二元体—三元体流变的形式分析。心理学家则更看重心理现象和心理功能的产生。特热沃森与托马塞洛之间的分歧似乎并不在于误解,而是在于对第二人称视角之第二重含义的权重赋予。特热沃森将初级主体间性视为更原始的社会认知能力,即婴儿可以在前语言、前符号、前思维乃至前社会化层面上识别另一个有意向的自主体;而托马塞洛坚持认为需要到第9个月。目前,对两种观点的判决还很难诉诸某一个关键性的实证证据。6个月大的婴儿已可区分速度、节奏、旋律、音调、重复等非内容、非意图的交流特征,当然按托马塞洛所言,这些与真正理解他人具有心智并无直接关系。沿思路往下,特热沃森认为前符号的交互性、同步性是更高阶的主体间性发展的基础;他之后诉诸交互的“音乐性”(musicality)概念以进一步澄清观点。二元行为的相互协调是社会交互的最基本的条件。与特热沃森类似的还有斯特恩,后者诉诸所谓“活力形态”(vitality forms)以讨论人类个体早期对非内容、非意图的运动学(或动力学)模式的感知;活力形态(行为如何展开的维度)构成了交互行为之内容和意图这两个维度的基础。近年来,关于活力形态等行为的运动学(或动力学)维度在人脑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实证确证,其中背侧中脑岛(dorso-central insula, DCI)被认为是一个活动中心。
形式社会学分析旨在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给出一般性的形式化理论框架,于是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差异因素被忽略了。本文在思考社会认知—社会网络连续性论题时初步考虑了社会单元构成成员的数量作为早期社会认知能力发展的约束条件的意义,这一条件也是泛文化而存在的,并不蕴含文化特殊性。需要指出,文化差异因素在第二人称视角的发展中必然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个体年龄增长,文化的权重将变得越来越大。但是,联合注意——本文概括为第二人称视角引导的对第三方对象的注意——一般被视为一种本能,托马塞洛将其视为区分人与其他一切动物(包括黑猩猩)的关键社会认知能力;联合注意固然可能因后天习得而存在人类个体能力强弱的差异(例如,有的儿童在课堂教学中受教师第二人称视角引导的学习能力更强),但是绝不会在正常人类个体身上出现全无的情况。此外,本文的重点考察对象是1岁以内的婴儿,其初级主体间性—次级主体间性能力的多重发展在这一阶段相应地受文化差异因素影响较少,于是文化的问题被视为次要的,被暂时搁置了。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往发展心理学历史上皮亚杰学派与社会文化历史学派之间的分歧在婴儿期联合注意的发生问题上得到极大的缓解,甚至出现解释上的趋同。于是,本文讨论的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有着发展阶段上的明确的有限性——就是以1岁以内的婴儿作为讨论对象。可知,当考虑1岁以上人类个体的第二人称视角的更多重含义时,文化因素需要被赋予更大的权重,甚至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结论二元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单元,因为其中涉及的二元交互并非必然蕴含关于二元体本身的总体性。理解这一要点对于区分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至关重要。关于第二人称视角与“社会”认知的关系:在当代哲学、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讨论中,第二人称被理解为社会认知和社会交互的基石。然而通过概念分析,第二人称首要地是关于“人”的,而非关于“社会的”人的。在第二人称视角的第一重含义中,“我”的唯一感知对象是“你”,此时的“我—你关系”可以脱离社会语境。在第二重含义中,“我”与“你”共同的感知对象是第三方的人或物。但是双方对第三方对象的联合注意依然是受第二人称视角直接引导的(“我”并不是脱离交互关系自主地注意这个对象)。关于二元体—三元体流变是否是相连续的,对该问题的讨论将继续下去。本文大致支持连续性立场,赞成特热沃森将主体间性处理为两阶段的多重性方案。不过,于社会认知基本能力的发展而言,前符号的、运动学或动力学维度如何连续地转化为符号的、内容和意图维度,是急需得到妥善处理的难题。
本文尝试将社会认知与社会网络两大领域知识合并到一起讨论,以实现互惠,这主要因为由上所述的社会认知以及所基于的第二人称视角是必然地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认知的前缀“社会的”并不是对认知之内涵的限定,以至于仿佛存在两种认知——一种是“社会的”,另一种是“非社会的”;可以说认知总是嵌入在社会中的,社会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社会中的个人和社会网络的感知。社会认知是什么——根本而言需要从它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的基本作用出发加以考察。
最后,本文只在二元交互和三元交互的语境中讨论第二人称视角的两重含义。在个体社会认知发展的更高级阶段,以及相连续地嵌入更复杂的社会网络和结构单元(以及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约束条件),第二人称视角还可能具有更多重含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何静:现象学访谈——第二人称式的双向建构
摘要:今天的现象学不只是一种概念化或技术化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和跨学科的方法在许多经验科学和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象学访谈技术的运用。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这种以第二人称式的双向建构为特征的访谈是“现象学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现象学访谈通过为那些待解释的问题提供关于个体经验的描述,能够推进对相关问题科学的和哲学的探究?要更好地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跨越现象学与科学之间的理论界限,以开放和包容的眼光重新审视(甚至拓展)那些现象学的主题。
关键词:事实变更 悬置 现象学访谈 第二人称 交互
作者何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0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1期P81-P90
责任编辑:王志强
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的现象学,主要起源于20世纪胡塞尔的思想,并在梅洛-庞蒂、萨特、古尔维奇(A. Gurwitsch)和舒茨(A. Schutz)等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获得了解释和发展。近几十年来,它在德雷福斯(H. Dreyfus)、加拉格尔(S. Gallagher)和扎哈维(D. Zahavi)等新现象学家的努力下,经历了持续的更新。
今天的现象学不只是一种概念化的或技术化的哲学,而是作为一种哲学的实践和跨学科的方法论。在许多经验科学的研究领域,如精神病学(Parnas et al. 2005)、心理学(Sass et al. 2017)、神经科学(Petitmengin et al. 2018)和病理学(Koch et al. 2013),以及关于公正(Weiss et al. 2020)、表演艺术(Montero 2015)和竞技体育(Ravn 2023)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表明,现象学不仅能够处理精深的哲学问题,而且能够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些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象学访谈(phenomenological interview)技术的运用。
尽管可能存在争议,但现象学访谈已成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的最主要方式。本文聚焦于这种新兴的访谈技术,旨在探究以下两个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这种以第二人称式的(second-personal)双向建构为特征的访谈技术是“现象学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现象学访谈通过为那些待解释的问题提供关于个体经验(singular experience)的描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科学和哲学探究?要更好地这些问题,就要求我们跨越现象学与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以开放和包容的眼光重新审视(甚至拓展)那些现象学的主题和方法论。
一、胡塞尔的先验分析与还原方法被视为现象学运动奠基者的胡塞尔聚焦于意识,将现象学看作“限制在纯粹直观中的……本质研究”。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现象学是关于本质(essence)的研究;其次,它限制在直观(intuition)中。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强调通过理性、抽象或辩证法等智力努力,抛开现象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胡塞尔同样关注事物本质,但他试图打破传统西方哲学中对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割裂,而强调要“朝向事物本身”,直接把握那些蕴藏在活生生现象中的本质。这是现象学的基本态度。
不难发现,这种基本态度赋予了现象与本质以新的内涵。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本质”概念,它不能被还原为实在的对象,而是浸润在现象中的、被当下情境所构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解中的“现象”概念,它蕴含着具有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特征。这种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独特张力,使得现象学不只描述现象或事态,而要通过对现象和事态的描述,去挖掘事物的结构特征、运作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条件。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果现象学始于对现象和事态的描述,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此过程中保持中立而不被可能存在的偏见所束缚呢?胡塞尔超越笛卡尔经验式的“我思”,效仿了康德的先验纲领。但不同于康德的先验演绎策略,胡塞尔认为我们要将自己置于一种先验的立场或态度中。处于这样一种先验立场,首先意味着要搁置“自然态度”。所谓“自然态度”,就是那些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关于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信念、态度、判断或形而上学的理论集合,例如,世界是实在的或者天下雨地就湿。无论在科学研究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自然态度中,并据此来理解事物。但在胡塞尔看来,想要从事一项严格的哲学研究,就不能以这种自然实在论为前提。由此,他强调暂时将那些作为我们理解事物出发点的自然态度搁置起来,是处于先验立场的第一步——悬置(epoché)。
悬置并不意味着要怀疑或颠覆那些关于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而是要将它们置于括号之中,不作判断。如扎哈维(D. Zahavi)所说,在悬置了自然态度后,我们“不再将实在看作无可置疑的出发点,转而开始关注世界中的对象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以及那些与对象相关的意向性行动和经验性结构”。由此,我们得到的是关于事物如其所示地显现给我们的持续体验,“世界并没有缩小,反而更丰富了……事物死而复生,重新出现,甚至连原先没看到的,都出现了。这时凡是能显现自身、能自身被给予的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可利用的认识对象”。换言之,在悬置之后的先验立场中,我们只描述我们体验到的现象,并由此进一步把握其本质。
这种辨识或洞察本质的方法就是本质变更(eidetic variation)。胡塞尔将这种本质变更看作基于想象力的概念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形式揭示了主体的经验结构和现象之间的深刻联系。简而言之,本质变更就是主体在摆脱了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后的反思过程,它将我们带入事物向我们如是展现自身的还原方式。例如,我可以想象我手中的杯子是红色而非白色的,可以想象它带手柄或不带手柄,也可以想象它是某个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我甚至可以在不同灯光下感受它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光泽……尽管我对杯子的体验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或者我的想象力而变得不同,但是到底是哪些特征使它成为一个杯子?如果在悬置了所有关于杯子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性判断后,那些未被悬置的、稳定的结构性特征令它成为一个杯子而非其他事物,那么这些特征的集合就构成了杯子的本质。
由此,悬置和本质变更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论。正如我们在上述例子中所见,杯子的本质不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术语或某种独立于意识的理念而获得解释;相反,它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在我们关于杯子的体验中直接地给予我们。尽管,现象学的方法仍然是一种对主体与(世界中)对象关系的分析方法,但是由于它聚焦于主体关于对象的体验,将分析从自然领域回到其先验基础,而获得了不同于其他哲学分析方法的独特性。
胡塞尔强调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是现象学之所以成为先验的哲学事业的核心要素。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悬置和本质变更,现象学家才能完成其首要的使命——“将世界中存在的普遍的显而易见性变得可理解”。由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象学不应当根据其研究主题来定义,而应当根据其独特的方法论来定义。如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出现了:一种恰当的现象学分析是否必须坚守包含了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论?换言之,一种淡化了悬置和本质变更的哲学探究还可能是现象学的吗?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试图表明:以加拉格尔和扎哈维为代表的新现象学,立足于先验现象学的理论立场,通过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甚至重新定义,探索了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互惠交流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推动了自然化的现象学运动,并由此为现象学访谈技术在经验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空间。
二、自然化的现象学及其对现象学方法的重新定义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篇文章中,胡塞尔将现象学称作“一门严格的科学”,主张要明确区分作为一种先验研究的现象学和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他试图使自己与康德(或批判哲学)、黑格尔以及浪漫主义(狄尔泰的浪漫主义解释学)之间建立联系,并远离一切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
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定义是:“自然主义是人们发现自然之后作为结果的一种现象……自然被看作时间—空间存在者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服从严格的自然法则……就自然主义者而言,他们只看到自然,而且主要是物理自然。任何东西要么本身是物理的,从而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体,要么作为一个随附在物理自然之上的变体,仅仅作为一个次要的‘平行的随附品’”。因此,自然主义蕴含了所有的事物都是物理的形而上学承诺,以及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理解一切事物的正当途径的方法论承诺。
需要明确的是,胡塞尔批判的是那种认为一切都可以得到自然科学解释的极端自然主义观点。更确切地说,他反对的不是自然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解释,而是那种将自然科学视为探究一切事物的唯一合法工具的自然主义取向。例如,他认为将意识以及规范(如数学、逻辑或观念)还原到单纯心理—物理过程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意识看作和火山、瀑布、石块类似的自然中的实体,而忽略了意识的先验维度。现象学需要排除的是那种自然主义的、单纯的经验分析过程,而一个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也就不可能是现象学家。
胡塞尔告诉我们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试图将我们从自然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也试图沿着笛卡尔和康德的脚步为自然科学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他坚信现象学可以完成这项使命:“每一种先验现象学的分析或理论(包括一种客观世界的先验构造理论),通过放弃先验态度可以在自然领域获得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悬置和本质变更的方法进入现象学立场,同时将基于现象学立场获得的洞见运用到科学中去。尽管对于胡塞尔而言,先验研究可能更为根本。但问题的核心似乎并不在于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何者更为根本,而在于两者是无法相互还原的不同类型的研究。胡塞尔认为,先验现象学的成果不应当被自然科学所忽视,而应当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看到,胡塞尔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既革命又保守,既独立又开放。更一般地说,这引出了关于现象学能否被自然化的持久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现象学是否应该与自然科学合作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现象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要明确区分先验研究的现象学和经验研究的自然科学,自然化后的现象学就不再是现象学了。但正如加拉格尔指出,从胡塞尔本人关于现象心理学的设想,到古尔维奇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运用,再到梅洛-庞蒂基于大量的心理学、病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对知觉进行的现象学分析,古典现象学家们事实上已经对现象学能否自然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以德雷福斯和加拉格尔为代表的新现象学家对以“计算—表征”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研究纲领不遗余力地批判,以及新一代具身认知研究纲领与经典现象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呼应,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关注现象学对于意识问题的独特思想洞见。另一方面,现象学家们也意识到:现象学所关注的意识论题同样也是其他经验科学的核心关切,现象学不应当忽视那些与这些论题相关的经验研究成果。同时,关于意识的哲学研究和经验研究在原则、方案和目标上相异,因此说后者会吞噬或取代前者是毫无意义的。如扎哈维所说:“宣称现象学应该从可用的最好的科学知识那里获得信息,同时坚持现象学的终极关注是先验哲学并且先验哲学不同于经验性科学,我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固守现象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严格界限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现象学仍然要保留其独有的特征和研究方法。
由此,今天关于现象学是否能被自然化的问题,更多地被转化为现象学如何与自然科学之间形成富有成效的互惠与合作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将现象学在意识研究上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纳入第三人称经验科学的研究框架中去。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自然化并非走向胡塞尔所批判的那种自然主义,而是面向一种被重新定义了的非还原主义的自然化。佩蒂托(Jean Petitot)等人提出:“所谓的‘自然化’,就是指将现象学整合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任何可接受的属性都与自然科学所承认的属性是连续的”。这暗示着,自然化的现象学不仅要将现象学洞见和方法运用于关于意识的经验研究中去,同时也要让现象学从经验研究的成果中受益并接受其挑战。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现象学对来自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开放和包容的。同时,现象学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拓展甚至重新定义先验哲学的基本方法论以便更好地与关于现象的实在论框架整合起来。在这方面,现象学家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方案。如前所述,本质变更是一种依赖主体想象能力的概念分析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主体的认知能力,而不同主体甚至同一主体在不同阶段和情境中的认知能力不尽相同。那么,我们的想象力是否足够可靠以帮助我们证实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呢?特别是在面对那些极其复杂的与意识相关的意向性、主体性以及时间性等问题的时候,本质变更就显现出了局限性,因为我们似乎很难通过想象来把握其丰富而精细的本质。
如果这样,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关于相关复杂现象的本质特征呢?加拉格尔提出,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转向经验或事实的变更(factual variation)以作为本质变更的补充或矫正策略。所谓事实变更,就是转向心理—病理学、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经验案例或模拟程序来帮助我们揭示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例如,一个拥有健全身体的人似乎很难想象缺失了身体部分肢体或感官以后的知觉和行动体验会是怎么样的,因此通过病理学中的幻肢现象来探究主体对身体的知觉体验可能会令我们受益匪浅。通过对真实病理学案例的讨论,可能促使我们回到最初的现象学描述以检验关于身体的知觉体验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模拟程序也可以作为我们想象能力的技术扩展,为现象学研究复杂的自组织的、非线性的和动力学的心智现象提供重要的支撑。正如福罗斯(Tom Froese)所说,运用这些模型来理解相关现象,像是现象学的“工作外包”(outsourcing),帮助我们超越人类主体在没有技术辅助的情况下单凭现象力开展工作的局限。
除了通过运用经验性的研究证据和模拟方案更新现象学对待解释事物的描述,加拉格尔主张通过“前载现象学”(front-loaded phenomenology)的方案推进现象学在经验性研究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他主张,现象学的洞见不仅用来应对相关实验结果的挑战和进行解释,还可以融入实验设计中以指导设计实验的范例(experimental paradigm)。这些洞见“可能来自胡塞尔式的先验研究,或者来自现象学的实验,或者来自更具经验导向的现象学分析。前载现象学并不意味着预设或自动接受由他人获得的现象学结果。相反,它要测试那些结果,更一般地说,它包含在一种以前从现象学中获得的洞见与(处于特定的实验或经验研究的目的)规定或扩展这些洞见的初步试验之前的辩证运动”。这是因为,实验设计总是涉及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背景假设,如果现象学的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谨慎、更细致地对待那些实验的概念和背景假设并提供新的灵感来源,那么实验设计就有可能较少受到已有理论预设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好的实验控制并令实验设计更贴近于真实经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前载现象学或现象学在经验科学中的运用过程必然涉及悬置或想象变更这样的现象学方法?在最近的一篇论文《应用现象学:为什么可以忽略悬置?》中,扎哈维指出:当一种方法声称自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方法,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现象学研究传统之间的关联;然而,如果现象学想要和经验科学间达成真正的互惠与合作,迫切需要我们将自己从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些技术性细节中解放出来。更明确地说,尽管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对于哲学现象学来说是重要的,但并不要求所有对现象学感兴趣或试图将现象学思维应用到经验研究中去的研究者都必须用到悬置和还原这样的现象学方法。事实上,“现象学并没有说现象学还原方法是一种简单、直接、不存在问题的方法。正是这样的考虑促使梅洛-庞蒂说:‘从现象学还原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胡塞尔总是不断地就还原的可能性质问自己的原因’”。在此意义上,经验科学研究对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并不在于研究者对所有已有理论的抛弃,也不在于仅仅对第一人称的经验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从根本上说,在于经验研究者能否运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从而捕捉到生活世界中关于主体经验的那些稳定的基础结构。
三、第二人称式的现象学访谈以加拉格尔、扎哈维为代表的现象学家通过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和重新思考,推动了自然化现象学运动的发展。在这一运动中,现象学不仅是哲学家对经典现象学著作和思想的诠释,也不仅是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质中所采取的进路,更是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和跨学科的实践,立足于现象学的主题与方法,为推动现象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而作出的努力。扎哈维这样描述现象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现象学也许在发展新的实验范例时提供帮助一样,现象学能够在对经验科学作出的基本理论假定发问并进行说明。经验科学也可以给现象学提供它不能简单忽略而必须能够调和的具体的研究结果,以及也许会促使现象学提炼或修改它自己的分析的证据”。
今天,现象学访谈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已经成为自然化现象学运动的具体展开方式,同时也成为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病理学等经验学科实现互动最主要的方式。长久以来,认知科学研究者们认为只有那些由外部实验观察者收集到的、可重复的实验数据才是科学的、可靠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现象学关注的增加,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第一人称的经验描述对于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佩蒂门金(Clair Petitmengin)等强调:在我们的经验中,有一部分是以一种“未被认识、未被注意或前反思(prereflective)的方式被体验的”,现象学访谈旨在通过具体的提示和问题触发这些经验,以帮助主体意识到经验中未被意识到的部分,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它们。
不过,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一项研究或一种方法论提供了关于主体的第一人称描述,我们就能把它称为现象学的吗?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聚焦于现象学访谈技术,探究这种以第二人称的双向建构为特征的访谈过程在何种意义上是“现象学的”。
一般而言,访谈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被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具有意识和能动性并且能够描述自身经历和感受的主体。加拉格尔和扎哈维强调,现象学访谈的目标“不是对特定的经验进行描述——‘这就是当下我所经验到的’——而是试图捕捉经验中那些不变的结构。在此意义上,它更像是科学而非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将主体看作一个特定的个体,并且诉诸主体关于为什么在当下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内省过程。在此意义上,现象学对那些不可检验、不可言说、不可比较的感受性(qualia)特征不感兴趣。现象学不关注心理过程(与行为过程或物理过程相对)。现象学关注的是现象的可能性和结构;它旨在探究经验的本质结构以及可能性的实现条件。现象学的目标是揭示在主体间(intersubjectively)可通达的结构,因此对这些经验的分析对任何(与现象相一致)的主体而言都是可修正和控制的”。
这就是说,一方面,现象学访谈聚焦于特定主体的经验描述以及呈现方式;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局限于特定主体描述经验的个体表征,而注重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挖掘这些特定主体的经验描述中隐藏的稳定的前反思结构。正是这种对前反思的经验结构的关注,而非对主体经验内容或语境的关注,令现象学访谈既不同于定性研究中常用的第三人称式的经验观察,也不同于第一人称的内省描述,而呈现出方法论意义上的独特性。
首先,现象学访谈是一种半结构化的(semi-structured)研究性访谈过程。访谈过程不是按照“建立假说—收集数据—验证理论构想”这样传统的定性研究思路展开的,而是通过悬置那些关于研究主题先入为主的信念、判断和理论,运用一些特定的开放式提问,将主体的注意力引导至对具体体验的关注,如“你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怎么样了”等。通过这样“没有内容但却由结构驱动”的更具体的提问方式,研究者帮助主体将对经验“是什么”(狭义的经验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如何”的问题(意识结构的完整行为)上来。
尽管主体的经验是私人的、稍纵即逝的、无法被直接追溯的,但却不是纯粹内在的东西,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而这些结构特征是可被挖掘或可通达的。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并不是在测试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或复述在过去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拥有的经验,而是聚焦于访谈过程本身,将主体的经验视为一个回忆、反思、描述甚至自我怀疑和否定中不断展开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主体可能需要在研究者的数次干预和引导下,才能在碎片化的意识流中发现自身经验的特征并提供相关的精细描述。因此,在现象学访谈开始以及进行过程中,研究者和被访谈者都无法预知访谈将会导向哪里或者形成何种结论。
其次,现象学访谈是一个第二人称式的双向建构过程。正因为它是一个半结构化的、高度开放的过程,所以才令这种双向建构成为可能。沙尔巴赫(Leonhard Schilbach)等提出了社会认知研究中的“第二人称”视角,即通过创造共同参与的实时交互情境,考察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真实互动过程及其结果。按照扎哈维的理解,第二人称式的交互以“互惠”(reciprocal)为主要特征:“第二人称视角涉及我和你的互惠关系,其中将你看作你的一个独特性在于,你也以一种第二人称的视角来看待我,也就是你将我看作你的你。在此意义上,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你——总是有两个主体存在。简而言之,采取第二人称的视角就是参与到一种主体—主体(你—我)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我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是他人的对象,一个被他人关注或交互的对象”。
不同于第三人称式的“主体—对象”的观察过程,在现象学访谈中的第二人称式的交互意味着研究者和主体作为彼此的“你”,共同参与到面对面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但要采取开放的态度,还要基于一种同感(empathy)的立场,与被采访者的经验和态度形成共鸣。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两个“你”通过语言、表情、手势、身体姿势和眼神等的具身性交互过程,积极参与并共同建构知识的生成过程。尽管主体的经验描述大部分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隐性的知识内容。这部分内容无法被涵盖在语言陈述中,而往往体现在主体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或者语音语调中。例如,某一陈述是以非常自信和肯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还是以含混而犹豫的方式传达的;或者主体在访谈过程中目光不再与研究者接触,而转向空旷的地方等。在这种情形中,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反复提问,进一步提升主体聚焦相关经验并提供细致描述的能力,帮助主体验证自身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并允许主体对自己之前的描述进行补充或修正。同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当一个问题得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会引导她修改下一个问题,或提出原先没有设定的新问题。因此,现象学访谈过程实际上是两个主体通过复杂的动态交互共同生成知识的过程。这种第二人称式的交互及其特定的情境,以建构性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主体双方语言和非语言性知识的生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学访谈所生成的经验描述实际上是由主体双方共同生成的描述。
最后,现象学访谈并不止于面对面的访谈过程,而延伸至研究者对主体经验描述进行的现象学分析过程。赫夫丁(Simon Høffding)和马丁尼(Kristian Martiny)强调现象学访谈从本质上作为一种知识的生成过程,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面对面的访谈本身,研究者生成对主体经验内容的描述;第二个层次是研究者运用悬置和想象/事实还原等现象学方法,对访谈中主体提供的描述进行检验,并将那些有效的经验描述作为现象学分析的出发点。
如前文所述,访谈是一个不断反复的、以第二人称的方式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描述的时间顺序和经验的时间顺序可能并不一致。当主体的经验在访谈中第一次被唤起的时候,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大网眼’(large-mesh)的描述。他需要在研究者的帮助下,反复多次才能意识到经验的连续性维度,并提供精细的网格性描述。因此,记录下来的报告就好像是由零散的经验描述组合成的拼图,研究者必须重新组织这些描述的顺序和样式”。这就要求研究者悬置那些来自自身专业背景的理论或者来自自身经验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对以文字、录音或视频等形式记录下来的主体描述进行重新组织、整理和精简,以形成更清晰的描述。正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对来自访谈的描述材料进行分析、反思和讨论,并进一步探究这些活生生的经验描述中所蕴藏着的稳定结构。当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会挑战已有的现象学洞见或者其主导的理论框架。
四、定性研究中的现象学访谈实例不同于第三人称式的经验观察,也不同于第一人称式的内省描述,现象学访谈通过以第二人称式的动态知识建构,获得主体关于特定生活经验的第一人称描述,并运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揭示那些隐含在活生生经验描述中的稳定经验结构。尽管现象学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哲学传统,但是我们看到在现象学访谈中,从半结构化的访谈设计,到第二人称式的访谈过程,再到对描述进行的现象学分析,都渗透着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并由此获得了其在现象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性和独特性。
近年来,现象学访谈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现象学方法被应用于认知科学、临床治疗以及其他与生活经验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并成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互惠合作的重要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以对竞技舞蹈定性研究中的现象学访谈为例,探究在何种程度上,现象学访谈通过为那些待解释的问题提供关于个体经验的描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相对应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果说,定量研究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定性研究解决的就是“为什么”的问题,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或行为,探究这些特征或行为产生的原因。这样的方法论特征,使得现象学访谈技术能够被广泛地运用于定性研究中。
在一项由南丹麦大学运动科学与生物机械中心主持的关于竞技舞蹈的定性研究中,丹麦舞蹈家比阳(Bjorn Bitsch)和阿什丽(Ashli Williamson)、米歇尔(Michelle Abildtrup)和马蒂诺(Martino Zanibellato)参与了现象学访谈。这两对竞技舞蹈的世界冠军不仅在训练过程和赛场上是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伴侣。他们每一天都要进行艰苦的专业训练,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保持世界冠军的竞技舞蹈水准。
选择对专业舞者进行现象学访谈的原因有:一方面,与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体运动的体验不同,专业舞者高度关注身体的运动过程并致力于将对它们的控制和表达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通过对竞技舞蹈案例的观察、定性分析和哲学反思,研究者希望深入探究主体对身体运动的感知能力。同时,莱文(Susanne Ravn)教授本人也曾是韵律体操运动员和专业舞蹈家,她的经历不但令她更容易与比阳和阿什丽、米歇尔和马蒂诺在访谈中的描述产生共鸣、共同生成经验描述,同时也有助于课题组对竞技舞蹈这项特殊联合行动的相关数据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
在2010年5月到7月,莱文教授及其课题组分别跟踪研究了比阳、阿什丽以及米歇尔、马蒂诺两对竞技舞蹈世界冠军的日常训练。他们大约跟随每对选手进行5—7天的训练,并在此期间分别对舞者进行时长约为1小时的两次访谈。莱文教授和课题组会预先设置一些开放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序列、内容和表述方式进行反复思考、确认,并且避免自己的经验和预设带入访谈而产生诱导性的作用。在访谈中,课题组要求比阳和阿什丽、米歇尔和马蒂诺根据自己作为专业舞者的经验来问题。这种研究者与舞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并不是研究者直接追溯那些隐匿在被访问者大脑或身体中的体验或知识的过程;而是通过回忆、反思、描述和质疑,将访谈变成一个经验之轴展开的过程——依据被访问者自身所提供的描述性信息,进一步通过提问等方式引导他们对自己在联合舞蹈中的行动和感受进行反思和描述。在描述过程中,舞者有时会用一些很技术性的词汇,有时又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体验。他们对舞蹈的不同描述,可能取决于舞蹈的类型,也可能取决于他们被访问时的精神状态(如,疲劳、兴奋等)。例如,他们用“舞蹈技巧”和“运动质量”来表达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是如何关注自身的身体运动。他们会用涉及“塑造”“时间控制”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身体动作。同时,在具体的训练中,他们还会特别关注如何能够将自身的运动流与舞伴的运动流相协调。当他们聚焦于质量方面的时候,会将注意力放在对每一个动作和步伐的具身感受以及对如何形成“共同起舞”的知觉体验。
在后续的数据分析阶段,研究者对来自访谈的记录脚本、录音、注释、反馈表、照片和视频等进行反复阅读、确认甚至质疑后,按照不同的主题内容进行整理。在最新的论文中,莱文教授基于来自现象学访谈的数据,运用本质还原和事实变更的方法,丰富并修正了现象学中关于前反思身体运动的相关讨论。
结语早在1912年,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在论文中就阐述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如何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受益。在现象学内部,从胡塞尔关于现象心理学的设想,到梅洛-庞蒂将来自心理学、病理学的经验研究成果作为现象学分析的重要灵感来源,再到加拉格尔和扎哈维等在自然化现象学运动中对经典现象学方法的拓展甚至重新定义,现象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实现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互惠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现象学访谈已经成为现象学与经验学科实现互动的重要方式。我们欣喜地看到,现象学访谈作为一种哲学实践,展现了现象学不断更新自身的思维方式去探究意识、世界以及胡塞尔所说的所有事物本身的努力;同时,现象学访谈还作为一种跨学科定性研究的工具,通过积极运用现象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呈现出不同于第三人称观察方法和第一人称内省描述的独特的方法论优势。但是,就研究现状而言,现象学访谈技术的应用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对研究人员的专业要求过高、应用领域有限、数据解释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访谈目标哲学化以及现象学分析肤浅等问题,亟待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究。
(本文注释内容略)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