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格策美文网
3招搞定《朱光潜诗论读书笔记》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05 1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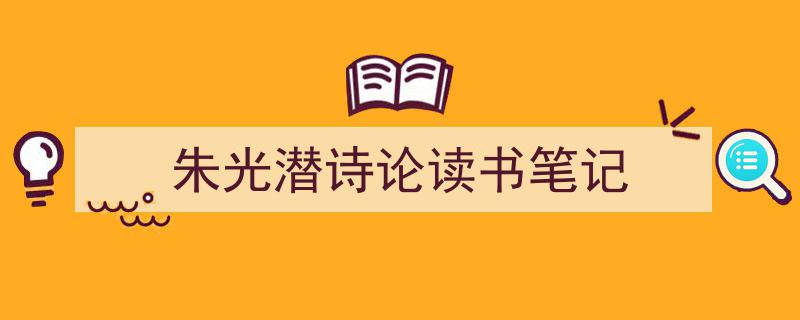
写作核心提示:
写一篇关于朱光潜诗论读书笔记的作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确定主题:首先,明确你的作文主题,即围绕朱光潜的诗论进行阐述。可以从他的某个观点、某个理论或某个作品入手,展开论述。
2. 理解朱光潜诗论:在动笔之前,要充分了解朱光潜的诗论,包括他的主要观点、理论体系以及代表作品等。这有助于你在作文中准确地引用和阐述他的观点。
3. 结构安排:一篇好的读书笔记作文,需要有清晰的结构。一般包括引言、主体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简要介绍朱光潜及其诗论;主体部分详细阐述你的观点,并引用朱光潜的诗论进行佐证;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4. 引用观点:在作文中,要准确引用朱光潜的诗论观点,并注明出处。这有助于增强作文的说服力。同时,要注意不要过度引用,以免影响自己的观点表达。
5. 结合实际:在阐述朱光潜的诗论时,可以结合实际例子进行说明。这样可以使你的观点更加具体、生动,有助于读者理解。
6. 分析评价:在作文中,要对朱光潜的诗论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既要肯定其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之处。这有助于展现你的批判性思维。
7. 语言表达:作文
说文解字系列之(212):朱光潜《诗论》述读(二):诗与谐隐
先生提出:文字游戏不外三种。一是用文字开玩笑,通常叫“谐”;二是用文字捉迷藏,通常叫“谜或”隐”;三是用文字组成很滑稽而声音很圆转自如的图案,通常无适当的名称,也可叫“文字游戏”。这三种东西在艺术诗或文人诗中也很重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特辟“谐隐”一章,可见古人对于这类作品也颇重视。
(1),诗与谐
所谓“谐”就是说笑话,乃喜剧之雏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以为中国戏剧源于巫与优。而“优”即以“谐”为职业内容。更早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也都提到过“优
的名称。优往往也是诗人。汉初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是著例。
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谐“最富于社会性,其雅俗共赏。刘勰释”谐”曰:“谐之言者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这就是说“谐”的社会性。社会的最好的团结力量是谐笑。尽善尽美的和穷极恶者都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者往往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的,往往就是谐趣的对象。如容貌的丑陋,品格的匮缺,人事的乖讹等。所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的。
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它是美感的而又不尽是美感的。说它是美感的,因为丑陋乖讹在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独立自足的意向。说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
第三,就谐趣本身来说,它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打动一时乐趣,也是沉闷世界中一种释放束缚的力量。可笑的事情究竟是丑拙鄙陋的,是人生中的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许多谐歌都以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故事。
谐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诗在有谐趣时,欢欣与哀怨往往共存,诗人的本领就在于能谐,即丑中见美,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所以说,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绪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泄剂。西方有曰:谐就是“对于命运开玩笑”,极是。中国诗人陶潜和杜甫是于悲剧中见诙谐者,刘伶和金圣叹是从喜剧中见诙谐者,嵇康、李白则介乎二者之间。
陶潜、杜甫都是伤心人而有豁达风度,表面上虽诙谐,骨子里却极沉痛严肃。如果把《责子》、《挽歌辞》之类的作品完全看作打油诗,就未免失去上品诗的谐趣之精彩了。
凡诗都难免有若干谐趣。情绪不外悲喜两端。喜剧中都有谐趣用不着说,就是把最悲惨的事当作诗来看待,也必在其中见出谐趣。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会作诗,也不能欣赏诗。诗和谐趣都是生气的富裕。不能谐是枯燥贫乏的症候,而枯燥贫乏的人和诗没有缘分。
当然,诗也是最不易谐的。因为诗最忌轻薄,而谐则最易流于轻薄。所以,同是诙谐,或为诗的盛境,或为诗的瑕疵,分别全在它是否出于至性至情。理胜于情者往往流于纯粹的讥讽。讥讽诗固自成一格,但是很难达到诗的盛境。
(2),诗与隐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里释“隐”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而“谜”为“回护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故“谜”在魏晋以后成了“隐”的化身。其实,“谜”与“隐”原本是一件东西。
谜语起源很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以产生。在中国,东汉许慎之“六书”中的“会意”,就是根据谜语的原则。中国最古的记载的歌谣是《吴越春秋》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者就是隐射“弹丸”的谜语。嗜好谜语是古代一种普遍的风气,甚至可以上升到“隐语之用,大者兴治济身”的地步。隐语的最早运用,大概在预言谶语。
隐语由神秘的预言变为一般人的娱乐以后,就变成一种谐。它与谐的不同只在着重点,谐偏重人事的嘲笑,隐则偏重文字的游戏。有时也合二为一。
隐语对诗的关系和影响是很大的。中国古代亦常有以隐语为诗者。例如古诗: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日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就是隐写“丈夫已出,月半回家”的意思。同时,隐语也是一种雏形的描写诗。民间许多谜语都可以看作描写诗看。中国大规模的描写诗是赋,赋就是隐语的化身。中国人似乎特别注意自然界事物的微妙关系和类似,对于它们 的奇巧的凑合特别感到兴趣,所以谜语和描写诗都特别发达。
而且,谜语不仅是中国描写诗的始祖,也是诗中“比喻”格的基础。包括歇后语,也是一种隐语。例如,“聋子的耳朵”(摆设)、纸糊灯笼"(一戳就破)之类。《诗经》中最常用的技巧是以比喻引入正文,如: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头两句就是隐语,所隐者有时偏于意象,有时偏于情趣,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情趣,这就是“兴”。
中国向来注诗者好谈“微言大义”,从毛苌做《诗序》一直到张惠言批《词选》,往往把许多本无深意的诗看作是隐射诗,固然不免穿凿附会。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诗人好做隐语的习惯,是有历史的。屈原用“香草美人”大半有所寄托,就是例子。诗人不直说心事而以隐语出之,大半有不肯说或不能说的苦处。在中国古代众多诗人中,李商隐的诗就是隐语的典型代表。
从技巧上来看,隐语在意义上的关联为“比喻”,而在声音上的关联则为“双关”。歌谣中用双关的很多。如:竹藁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炭”与“叹”双关)类似的例子很多。
唐以后文字游戏的风气日盛,诗人常爱用人名、地名、药名等作双关语。例如:鄙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钩帘阴卷柏,障壁坐防风。客土依云惯,流泉架木通。行当归老矣,已逼白头翁。(《漫叟诗话》引孔毅夫诗句)其中“防风”、“甘草”就是中药材名称。
总之,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为规模最大,赋即源于隐。后来咏物诗词也大半根据隐语原则。诗中的比喻(诗论家所谓的比、兴)以及言再此而意在彼的寄托,也都含有隐语的意味。就声音说,诗用隐语为双关,则一切神话寓言和宗教仪式以至文学名著大半都是隐语的变形,都各有一个“谜底”的。
说文解字系列之(237):朱光潜《诗论》述读(五)——诗与散文
诗与散文究竟有无区别?区别何在?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加以讨论的。
(1)音律与风格上的差异
写诗认为:中国旧有“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说法,换言之,“有韵律的是诗,无韵律的是散文”,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诗不必尽有韵律,有韵律也不尽是诗。如全凭空洞的形式,则《百家姓》、《千字文》、医方脉诀等可列于诗,而散文名著,如《史记》、柳子厚的山水杂记、《红楼梦》之类,虽无韵律而有诗的风味的作品,反被摈于诗的范围以外。故韵律说,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种说法是,诗与散文在风格上应有分别。散文偏重叙事说理,其风格应直截了当,明白晓畅;而诗偏重抒情。在一般人看来,散文和诗中间应有一个界限,不可互越,散文象诗如齐梁人作品,是文之弊;诗象散文,如韩愈及一部分宋人的作品,亦非上乘。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诗和散文风格之不同,也正如这首诗和那首诗的风格不同,所以,风格的不同也不是区分诗和散文的好标准。
先生认为,我们不能说诗在风格上高于散文。诗和散文各有妙境,诗固往往能产生散文所不能产生的风味,散文也一样。
先生举例说,《世说新语》有一段文字:“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耶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这段散文,零零数语,写尽人物俱非之伤感,多么简单而又隽永。而庾信在《枯树赋》中把它译为韵文说:“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的文字比起原文,一方面纤巧些,另一方面也较呆板些。原文中既直接而又飘渺摇曳的风致在《枯树赋》的整齐合律的字句中就失去了大半。
其次,诗词的散文序有时也胜于诗本身。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王羲之的《兰亭诗》、以及姜白石的《扬州慢》词,虽然都很好,但风味隽永,似较序文稍逊一些。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诗的风格不必高于散文。
(2)诗与散文实质上的差异
形式既不足以区分诗与散文,然则实质如何?有人说,诗有诗的题材,散文有散文的题材。就大体来说,诗宜于抒情遣兴,而散文则宜于状物叙事说明。极好的言情作品都要在诗里找,极好的叙事说明的作品都要在散文里找。
先生认为:诗与散文的分别就只能在情与理方面见出。散文只宜于说理的观念,是一种传统的偏见。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还是散文,里面都必有它的特殊情趣。比如,许多小品文是抒情诗。许多可以用诗表现的情趣,在小说里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一个作家用诗或散文来表现他的意境,大半取决于当时的风尚。荷马和莎士比亚如果生于现在,也一定会写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劳伦斯诸人如果生活在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代,也一定会写史诗或悲剧。诗除情趣之外,也都有几分理的成分,所不同的是它的情理融为一体,不易分开罢了。
所以,从题材性质上区别诗与散文,并非绝对的可靠。
(3)否认诗与散文的区别
有人认为:凡是具有纯文学价值的作品都是诗,无论它是否具有诗的形式;凡是有创造性的文字都是纯文学,凡是纯文学都是诗。所以,所谓“诗”就包含一切纯文学,而“非诗”就包含一切无文学价值的文字。
先生也不完全同意此说。先生认为,在纯文学的范围内,诗和散文仍有区别。一切艺术都可以叫做诗,是因为一切艺术到精妙处都必有诗的境界。诗和诸艺术,诗和纯文学,都有共同的要素。但是,它们在相同之中也还有不同者在。比如王维的画、诗和散文尺牍,虽然都同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为他的个性流露;但是在精妙处,可见于诗者不必见于画,也不必尽可见于散文尺牍。诗与散文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还是有区别的。
(4)诗为有音律的纯文学
大体上说,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一般来讲,散文的功用偏于叙事说理,诗的功用则偏于抒情遣兴。事理直截了当,一往无余,情趣则低徊往复,缠绵不尽。直截了当者宜偏重叙述语气,缠绵不尽者宜偏重惊叹语气。在叙述语中,事尽于词,理尽于意;在惊叹语中,语言是情感的缩写字,情溢于词,所以读者可以因声音而想到弦外之音。换言之,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则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诗的情趣是缠绵不尽,往而复返的,诗的音律也是如此。
先生认为,把诗说成是“有音律的纯文学”,也还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有和无是一个绝对的分别,就音律论,诗和散文的分别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诗必有固定的音律,但自由诗的音律就不严格。诗可以由原来极严谨明显的规律,经过不甚显著的规律,到现在已经少有规律了,除了一些今人所作的旧体诗词。
次就散文而论,他也并非绝对不能有音律的。诗早于散文,散文是由诗解放出来的。在初期,散文的形式和诗相差不远。秦汉以前的散文,常杂有音律在内。试举一例: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
这是一段散文,但是都有音律。再如赋,它就是诗和散文界线上的东西:流利奔放,一泻而下,似散文;于变化多端之中仍保持若干音律,又似诗。隋唐以前的大部分散文都没有摆脱诗赋的影响。唐代古文运动,也实在是散文解放运动。以后,流利轻便的散文逐渐占优势,不过,诗赋对于事物的影响直到明清时代还未完全消灭,骈文八股可以为证。
总之,诗和事物在形式上的分别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诗和散文两国度之间有一个很宽的叠合部分作界线,在这界线上有诗而近于散文,音律不甚明显的;也有散文而近于诗的,略有音律可寻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有音律的纯文学”诗诗的精确的定义。
二是,这定义假定某种形式为某种实质的自然需要,也很值得商榷。我们先来看两首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
香馥馥,樽前有个人如玉,人如玉,翠翘金凤,内家装束。娇羞爱把眉儿蹙,逢人只唱相思曲。相思曲,一声声是:怨红愁绿。(周邦彦《忆秦娥》)
两首词都是用一个相同的词牌名,但在情调上,它们绝不相同。李词悲壮,有英雄气;周词香艳,尽是儿女气。由此可知形式与实质并无绝对的必然关系。文学史上,词调甚多,常用的也就一二百个。诗人须用这些有限的形式来范围千变万化的情趣和意象。如果形式和内容有绝对的必要关系,那么,每首诗就必须自创一个格律,绝不能不同的诗人、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情境而使用同一个词牌了。
再者说,诗也不全是自然流露。就是民歌也有它的传统的技巧,也很富于守旧性。比如,它也填塞不必要的字句(诗歌上的术语叫“衬字”)来凑数,用意义不恰当的字来趁的,模仿以往的民歌的格式。也就是说,民歌的形式也还是现成的、外在的、沿袭传统的,也不全是自然流露的结果。
(5)形式沿袭传统与情思语言一致说不冲突
先生认为,承认形式是沿袭的,与承认情感思想语言一致,并不相悖。
第一,诗的形式是语言的纪律化之一种,其地位等于文法。语言有纪律化的必要,其实由于情感思想有纪律化的必要。文法与音律都是人类对于自然的利导与征服,在混乱中所造成的条理。一切艺术的学习都必须经过征服媒介困难的阶段,不独诗于音律为然。
其次,诗是一种语言,而语言生生不息,却亦非无中生有。语言的文法常在变迁,任何语言的文法史都可以证明,但每种变迁都从一个固定的基础出发,而且它向来只是演化而不是革命。诗的音律与文法一样,它们原来都是习惯,但是也是做演化出发点的习惯。诗的音律在各国都有几个固定的模型,而这些模型也随时随地在变迁。所以,诗的音律有变的必要,就因为固定的形式不能应付生展变动的情感思想。如果情感思想和语言可以不一致,则任何情感思想都可纳入几个固定的模型里,诗的形式便无变化的必要。
(6)诗的音律本身的价值
诗与散文的疆域都在不断扩大,这是事实。徐志摩如果生活在六朝,也许会用赋体来写《死城》和《浓得化不开》。所以,西方有人说,一个作家采用诗或散文来表现他的情感思想,大半取决于当时的风尚。
诗的形式纵然是沿袭传统的,它一直流传到现在,也自然有它的内在价值。它将来也许不至于完全被散文吞并。艺术的基本原则是“寓变化于整齐”,诗的音律好处之一,就在给你一个整齐的东西做基础,可以让你去变化。散文入手就是变化,变来变去,仍不过是无固定形式。诗有格律可变化多端,所以诗的形式比散文的实较繁富。
此外,音律的最大的价值自然在它的音乐性。音乐自身是一种产生浓厚美感的艺术。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