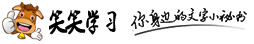欢迎来到格策美文网
3招搞定《媒人在婚礼上最短讲话》写作。(精选5篇)
更新日期:2025-05-15 17:15

写作核心提示:
媒人在婚礼上最短讲话作文,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 "明确目的": - 确保讲话内容围绕祝福新人的主题,表达对新人美好未来的祝愿。
2. "简洁明了": - 由于是最短讲话,语言要精炼,避免冗长和复杂的句子。
3. "情感真挚": - 虽然短,但情感要真挚,能够触动人心,让在场的宾客感受到喜悦和温馨。
4. "内容相关": - 讲话内容应与婚礼主题相关,可以提及新人的爱情故事、家庭背景或者双方共同的愿望。
5. "尊重文化习俗": - 如果有特定的婚礼习俗或传统,讲话中应适当融入,以示尊重。
6. "以下为具体注意事项":
- "开头":直接表达祝福,例如:“亲爱的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我谨代表双方家庭,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祝福!”
- "正文": - 简要回顾新人的爱情故事,如:“他们相识于校园,相恋于青春,终于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 表达对新人的期望,如:“愿他们携手共度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相互扶持,白头偕老。” - 如果可能,可以加入一些幽默
奔赴千里参加大姑儿子婚礼,我们在她家睡了几天地铺后,大姑哭了
函是在春分那天到的,薄薄一张纸,大姑的字体倾斜而坚定,像是她站在老屋门口那微微前倾的身影。
"表哥结婚了,大老远的,你们方便来吗?"妻子小心翼翼地问,她知道我和老家亲戚联系不多。
我望着窗外飘落的杨絮,心中翻涌起久远的回忆。
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十岁那年,父亲所在的纺织厂开始裁员,家里顿时一筹莫展。
彼时,城里人还在用粮票买米,肉票买肉,柴米油盐样样都要计较。
母亲每天算计着家里所剩无几的票证,愁得头发一把一把地白。
是大姑二话不说,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接我去县城,让我在她家住了整整一个学期。
"弟妹,你先顾家里,孩子交给我。"大姑当时这样对我母亲说,"咱老王家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清楚记得那时候大姑家的情形:两室一厅的砖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夏天乘凉特别舒服。
大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那口铁锅给我煮稀饭,再炒一个鸡蛋,说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着"。
我和妻子商量着定下了行程。火车票是硬座,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
"买软卧吧,坐那么久多受罪。"妻子建议道。
我却摇头拒绝,心里想着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多带点礼物。
"咱们带什么礼品好呢?"妻子翻着日历,"大姑年纪大了,要不带些补品?"
我想了想,拿出存折取了五千块钱。
"太多了吧?"妻子瞪大了眼睛。
我摇摇头,"大姑膝下就这一个儿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表哥结婚是大事,这钱应该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考上城里的大学,交学费时手头紧,又是大姑默默寄来了五百块,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火车窗外,城市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田野和山脉。
列车上挤满了人,走道里站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和汗水的味道。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带着孩子回老家的夫妻,孩子哭闹着要吃糖,妻子从包里掏出一块水果糖,我恍惚间想起小时候大姑也经常在口袋里藏着几颗水果糖,说是"给乖孩子的奖励"。
火车到站时已是傍晚,县城变了模样,马路宽了,楼房高了,唯独火车站依旧那般破旧。
出站口,我一眼认出大姑——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全白了,后背有些驼,却依然站得笔直,像山里那些经风雨却不肯弯腰的老松树。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大姑接过我们的行李,眼里闪着光,手上的老茧刮得行李袋发出沙沙的声响。
"瘦了些,城里工作忙吧?要不要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大姑的声音有些颤抖,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仿佛要把我的模样牢牢记住。
"不饿,大姑,咱们直接回家吧。"我说着,注意到大姑脸上的皱纹比上次见面时又深了些。
大姑拦了一辆面的,我们挤在后座上,车子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前行。
窗外,夕阳将整个小城染成金黄色,街边的梧桐树影子拉得老长,一排排自行车整齐地停在路边。
"现在县城富啦,家家户户买得起冰箱彩电了。"大姑指着路边的电器商店,"听说你们城里都用上电脑了?我们这儿也有网吧,你表哥天天往那儿钻。"
大姑家还是那个两居室的老房子,墙皮有些剥落,但打扫得一尘不染。
院子里的柿子树长得更高了,树下摆着几把竹椅,邻居老刘正坐在那乘凉,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是小辉回来了吧?长这么高了,上回见你还是你考大学那年呢!"
客厅里,大姑丈正在和几个老邻居搓麻将,烟雾缭绕中,他抬头招呼了一声就继续埋头算牌。
屋子里的布置几乎没变,还是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那张有些褪色的沙发,那个刻着花纹的木茶几。
唯一新添的,是茶几上放着的一台老式录音机,正轻声播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
"你们睡小屋,我铺了新褥子。"大姑领我们进卧室,却见里面摆满了喜糖喜饼和各种婚礼用品。
床上堆满了红色的被褥和几件崭新的衣服,墙上贴着大大的"囍"字。
"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屋子乱,你们将就睡客厅地铺几晚。"大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让你们住宾馆的,可你表哥说家里有地方,不用花那冤枉钱。"
我赶紧说:"大姑,您别担心,我小时候还在你家地上打过地铺呢,咱们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
大姑闻言,眼眶一下子红了,转身假装整理东西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去做饭,你们先休息会儿。"大姑说着匆匆走出屋子。
夜里,躺在硬邦邦的地铺上,我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自行车铃声和远处广播站播放的音乐,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陌生。
我想起小时候大姑家那张木板床,睡着也是硬邦邦的,可那时心里却满是踏实。
"睡不着?"妻子轻声问。
"在想小时候的事。"我翻了个身,"那时候大姑对我特别好,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怕我想家。"
妻子笑了笑:"你大姑是个好人,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特别亲切。"
"那时候大姑和大姑丈日子也不宽裕,表哥还小,家里就那点工资,却从不让我感到委屈。"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大姑半夜三更背着我去医院,第二天天不亮又去上班,那会儿她在县棉纺厂做工,一天三班倒。"
妻子握住我的手:"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好好陪陪大姑。"
第二天一早,我被厨房里的声音吵醒。大姑已经在忙活了,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伴着炒菜的香气飘进客厅。
我悄悄起身,看见大姑正弯腰在灶台前忙碌,苍老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单薄。
"大姑,我来帮忙。"我走过去。
大姑吓了一跳:"怎么起这么早?昨晚睡得好吗?地上硬不硬?"
"睡得挺好的,比我想象的舒服多了。"我笑着接过她手中的铲子,"您歇会儿,让我来炒菜。"
"你会什么啊,城里少爷。"大姑嗔怪道,却也乐呵呵地坐到一旁的小凳子上。
"今天是表哥的婚礼?"我一边翻炒着锅里的青菜,一边问。
"嗯,上午九点开始,在新华饭店,县城最气派的地方。"大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你表哥这次找的媳妇是镇上会计的闺女,模样俊,又有文化,就是家里要的彩礼有点多。"
我注意到大姑说到彩礼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来。
"管他呢,儿子结婚是大事,花点钱值得。"大姑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干果,"这是我做的零嘴,你最爱吃的,尝尝看还合不合口味。"
我接过来,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蜜饯山楂和糖炒栗子,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满是儿时的味道。
第二天是表哥的婚礼。县城最大的饭店里,摆了八十桌酒席,一眼望不到头。
大厅正中央悬挂着巨大的"囍"字,红色的气球和彩带装点着整个空间,一台老式录音机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和妻子被安排在主桌,表哥西装革履,显得精神抖擞;新娘一袭白纱,头上戴着发箍,看起来很是般配。
婚礼是按照老传统办的,先由媒人致辞,然后新人给长辈敬茶,最后切蛋糕放鞭炮。
大姑站在一旁,穿着她最好的一套深蓝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年轻了十岁。
她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给每张桌子都添茶倒水,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席间,我遇到了小时候的邻居李叔。他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身子骨却依然硬朗。
"小辉啊,在城里混得咋样?"李叔给我倒了杯酒,声音洪亮。
"还行,就是忙,很少回来看看。"我有些惭愧地说。
酒过三巡,李叔悄声告诉我:"你大姑为了这婚事,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女方家要十万块彩礼,你知道你大姑是哪来的钱吗?"
我摇摇头,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把家里那对黄花梨木的箱子卖了,还有你爷爷留下的那块玉佩,都换了钱。"李叔叹了口气,"那箱子可是她奶奶传下来的,一直当宝贝似的供着,谁摸一下都不行。"
我心里一紧。那对黄花梨木箱是大姑成亲时带来的嫁妆,是她最珍视的东西,平时连灰尘都不让落上一点。
爷爷的玉佩更是家族传下来的宝贝,据说是清朝末年的东西,爷爷生前曾说要传给下一代。
"这彩礼钱,你大姑一个人包了大头。"李叔又说,"现在这年头,娶个媳妇不容易哟,没有几万块彩礼,姑娘都不肯嫁。"
我沉默不语,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婚宴上,我注意到表哥媳妇对大姑的态度有些冷淡。大姑端茶送水,新媳妇只是点点头,连句谢谢都没有。
有一次大姑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水,新媳妇皱着眉头说了句:"慢点慢点,别把我的裙子弄湿了。"
语气里带着不耐烦,仿佛大姑不是长辈,而是个做错事的下人。
我有些不舒服,但想到今天是喜日子,也就忍了。
妻子坐在我旁边,捏了捏我的手:"别往心里去,新媳妇可能是紧张。"
席间有人来敬酒,我借机观察大姑丈。他依然沉默寡言,眼神却比以前更加黯淡。
他和大姑的婚姻在当地算是传奇——三十多年前,大姑原本可以嫁给县城一个干部,却因为爱情选择了当时只是个普通工人的大姑丈。
如今大姑丈已经退休在家,每天不是搓麻将就是看电视,很少帮大姑分担家务。
婚宴结束后,我们回到大姑家。大姑忙着收拾东西,妻子主动上前帮忙,两人在厨房里有说有笑。
我趁机去了大姑卧室,想把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刚进门,就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我十岁时的照片,穿着大姑给我买的那件蓝色毛衣,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相框旁边放着一个小布包,我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火车票,仔细一看,全是大姑这些年来看我的车票,从我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张不落地保存着。
我的眼眶湿润了,赶紧把钱塞到枕头底下,悄悄退了出来。
第三天清晨,我起床时发现大姑已经在厨房忙活了。炒鸡蛋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恍惚间,仿佛回到了童年。
"快洗脸,趁热吃,"大姑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铺着一层金黄的鸡蛋,还撒了些葱花,"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记得不?"
我点点头,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大姑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慈爱。
"吃饱了吗?再来一碗?"大姑问。
"够了够了,再吃就要撑死了。"我笑着推开碗。
大姑收拾碗筷,我帮她把餐桌擦干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大姑花白的头发上,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对了,听说表嫂家条件不错?"我状似随意地问。
大姑点点头:"她爹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家里有些积蓄,人家姑娘又懂事,就是要的彩礼高了点。"
"十万块呢。"我小声嘀咕。
大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谁跟你说的?是不是老李那个大嘴巴?"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钱嘛,花了就花了,儿子娶媳妇是大事。"大姑摆摆手,像是不在意似的,"你表哥这辈子就这一次婚姻,得风风光光的。"
午后,大姑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旧棉袄,递给我:"看看,还认得不?"
我一眼认出那是我小学时穿的,肘部已经磨白了,袖口还有大姑缝补的痕迹。
"你还留着这个?"我有些惊讶。
"舍不得扔,"大姑抚摸着棉袄,"那年你爸下岗,你来我这住,就穿这件。那时你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看着心疼。"
她顿了顿,眼神变得柔和:"现在好了,自己有出息了,老了也有靠了。"
大姑又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我小时候用过的铅笔盒、课本,还有一张我画的画,歪歪扭扭地写着"大姑好"。
"这些都是你的宝贝,我都给你留着呢。"大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捧在手心,像对待什么稀世珍宝。
晚饭后,表哥和他新婚的妻子来大姑家串门。表嫂穿着一件鲜亮的红色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一看就价值不菲。
"妈,我们明天就搬新家了。"表哥说,"你和爸要不要搬过去住几天?"
我听出表哥的意思是想让大姑去帮忙收拾新房子。
"不用不用,你们小两口自己住。"大姑摆摆手,"妈这几天还要招待你表弟呢。"
表嫂撇撇嘴:"那等你们走了,妈再来帮我们收拾收拾?"
大姑连连点头:"行行行,到时候我去帮忙。"
表哥和表嫂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前表嫂还不忘提醒大姑:"妈,明天早上我们去买窗帘,你要是有空就一起去给参谋参谋。"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有些堵。表哥从小被大姑宠着,如今成家了,想的却只是让大姑去帮忙干活。
"表哥在哪儿工作啊?"我问大姑。
"县里印刷厂,去年刚转正,工资不高,但有个铁饭碗。"大姑脸上带着骄傲,"他媳妇在银行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有五六千呢。"
在县城,这确实算是不错的收入了。我想起大姑为了凑彩礼卖掉的老物件,心里更不是滋味。
第四天晚上,我和妻子收拾行李准备明天返程。
妻子小声告诉我:"我看到大姑的枕头底下压着钱,她一直没动。"
我叹了口气:"大姑这辈子就是这样,给别人的从来不手软,自己的却一分都舍不得花。"
半夜里,迷迷糊糊间我听见客厅有动静,睁眼看到大姑端着一盆热水站在地铺边。
她的动作很轻,生怕吵醒我们:"地上凉,泡泡脚暖和些。"
我假装刚醒:"大姑,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
大姑有些不好意思:"看你们睡地铺,心里过意不去。这么大人了还睡地上,委屈你们了。"
月光从窗帘缝隙照进来,我看见大姑的眼角有泪光闪动。
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我的被角,确认没有露出来,才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
"大姑,您坐会儿吧。"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大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来。
"睡不着?"她问。
"想起小时候的事了。"我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家里停电,您点着蜡烛陪我做作业,还给我讲故事。"
大姑笑了:"那时候你胆子小,一到晚上就怕黑,非要我陪着。"
"大姑,"我突然问道,"您当年为什么不去省城?"
大姑沉默了一会儿:"当时你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没人照顾。再说了,调到省城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得工作,还要适应新环境。在家乡,好歹有亲戚朋友,日子过得踏实。"
"可您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几分。
"嘘,小声点,别吵醒你媳妇。"大姑拍拍我的肩膀,"生活就这样,没什么好不好的,开心就行。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儿子成家了,你也有出息了,比什么都强。"
她站起身,轻轻擦了擦眼角:"时候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送你们。"
那一刻,许多往事如潮水般涌来。我想起大姑年轻时有机会调到省城工作,却因为要照顾瘫痪的爷爷奶奶而放弃;想起她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总是留给别人,从不计较回报;想起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摸过多少人的伤痛与困难。
大姑的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却从不曾抱怨一句。
临行那天,我找了个借口单独和大姑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存折,塞到她手里:"大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大姑丈年纪大了,要多保重身体。"
存折里有两万块钱,是我和妻子商量后又加了些。大姑拿着存折,愣在原地。
"这是干啥?"她有些不知所措,想要推辞。
我握住她的手:"大姑,我记得您说过,世上最宝贵的不是钱,是亲情。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这点钱不算什么,您就收下吧,当是我这个侄子的一点心意。"
大姑的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傻孩子,"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你自己留着用吧,大姑不缺钱。"
"我知道您不缺,但我想给您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我坚持道,"您这辈子为别人付出太多,也该为自己活活了。"
大姑终于没再推辞,小心翼翼地把存折放进衣兜里:"行,那大姑就收下了。等你下次回来,我做好吃的给你。"
火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我看见站台上大姑的身影渐渐变小。她一直站在那里,挥舞着手臂,直到看不见为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最深沉的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不是花言巧语的表白,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天;在你迷失的时候,有盏灯为你指引方向;在你成长的路上,有人默默付出,从不求回报。
回城后的第一个月,我给大姑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大姑的声音依然温和:"最近工作忙不忙?吃得好不好?"
我笑着:"都挺好的,大姑,您呢?"
"我能有啥不好的,就是你表嫂怀孕了,每天都要我去帮忙做饭洗衣服。"大姑说着,却听不出半点抱怨,反而充满了期待,"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当太姥姥了,想想就高兴。"
电话那头传来表嫂的声音:"妈,水开了没有?"
大姑匆匆说了句"回头再聊",就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心里五味杂陈。那笔钱,不知道大姑最后有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大姑亲手织的一件毛衣,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孩子,大姑很好,你别惦记。你给的钱,我用来买了台缝纫机,打算给村里孩子们做些衣服。记得常回家看看,大姑等你。"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张照片,是大姑站在她家门口,怀里抱着一台老式缝纫机,笑得像个孩子。
我拿着照片,眼前浮现出大姑在火车站挥手的身影,还有她凌晨三点起来给我端热水时眼角的泪光。
大姑的眼泪,是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为了家人默默付出,却从不愿让泪水成为别人的负担。
这就是亲情,朴实无华,却胜过世间一切。
我想,来年春天,我还要回去看看大姑,陪她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乘凉,听她讲那些过去的故事,看她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舒展开来,像一本厚重的生活史诗,记录着平凡人生中最不平凡的爱。
奔赴千里参加大姑儿子婚礼,我们在她家睡了几天地铺后,大姑哭了
函是在春分那天到的,薄薄一张纸,大姑的字体倾斜而坚定,像是她站在老屋门口那微微前倾的身影。
"表哥结婚了,大老远的,你们方便来吗?"妻子小心翼翼地问,她知道我和老家亲戚联系不多。
我望着窗外飘落的杨絮,心中翻涌起久远的回忆。
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十岁那年,父亲所在的纺织厂开始裁员,家里顿时一筹莫展。
彼时,城里人还在用粮票买米,肉票买肉,柴米油盐样样都要计较。
母亲每天算计着家里所剩无几的票证,愁得头发一把一把地白。
是大姑二话不说,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接我去县城,让我在她家住了整整一个学期。
"弟妹,你先顾家里,孩子交给我。"大姑当时这样对我母亲说,"咱老王家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清楚记得那时候大姑家的情形:两室一厅的砖房,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夏天乘凉特别舒服。
大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那口铁锅给我煮稀饭,再炒一个鸡蛋,说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着"。
我和妻子商量着定下了行程。火车票是硬座,二十多个小时的路程。
"买软卧吧,坐那么久多受罪。"妻子建议道。
我却摇头拒绝,心里想着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多带点礼物。
"咱们带什么礼品好呢?"妻子翻着日历,"大姑年纪大了,要不带些补品?"
我想了想,拿出存折取了五千块钱。
"太多了吧?"妻子瞪大了眼睛。
我摇摇头,"大姑膝下就这一个儿子,一辈子省吃俭用,表哥结婚是大事,这钱应该的。"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考上城里的大学,交学费时手头紧,又是大姑默默寄来了五百块,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火车窗外,城市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田野和山脉。
列车上挤满了人,走道里站着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和汗水的味道。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带着孩子回老家的夫妻,孩子哭闹着要吃糖,妻子从包里掏出一块水果糖,我恍惚间想起小时候大姑也经常在口袋里藏着几颗水果糖,说是"给乖孩子的奖励"。
火车到站时已是傍晚,县城变了模样,马路宽了,楼房高了,唯独火车站依旧那般破旧。
出站口,我一眼认出大姑——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全白了,后背有些驼,却依然站得笔直,像山里那些经风雨却不肯弯腰的老松树。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大姑接过我们的行李,眼里闪着光,手上的老茧刮得行李袋发出沙沙的声响。
"瘦了些,城里工作忙吧?要不要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大姑的声音有些颤抖,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仿佛要把我的模样牢牢记住。
"不饿,大姑,咱们直接回家吧。"我说着,注意到大姑脸上的皱纹比上次见面时又深了些。
大姑拦了一辆面的,我们挤在后座上,车子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前行。
窗外,夕阳将整个小城染成金黄色,街边的梧桐树影子拉得老长,一排排自行车整齐地停在路边。
"现在县城富啦,家家户户买得起冰箱彩电了。"大姑指着路边的电器商店,"听说你们城里都用上电脑了?我们这儿也有网吧,你表哥天天往那儿钻。"
大姑家还是那个两居室的老房子,墙皮有些剥落,但打扫得一尘不染。
院子里的柿子树长得更高了,树下摆着几把竹椅,邻居老刘正坐在那乘凉,见了我连忙站起来。
"是小辉回来了吧?长这么高了,上回见你还是你考大学那年呢!"
客厅里,大姑丈正在和几个老邻居搓麻将,烟雾缭绕中,他抬头招呼了一声就继续埋头算牌。
屋子里的布置几乎没变,还是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那张有些褪色的沙发,那个刻着花纹的木茶几。
唯一新添的,是茶几上放着的一台老式录音机,正轻声播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
"你们睡小屋,我铺了新褥子。"大姑领我们进卧室,却见里面摆满了喜糖喜饼和各种婚礼用品。
床上堆满了红色的被褥和几件崭新的衣服,墙上贴着大大的"囍"字。
"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屋子乱,你们将就睡客厅地铺几晚。"大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让你们住宾馆的,可你表哥说家里有地方,不用花那冤枉钱。"
我赶紧说:"大姑,您别担心,我小时候还在你家地上打过地铺呢,咱们自家人不用这么客气。"
大姑闻言,眼眶一下子红了,转身假装整理东西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去做饭,你们先休息会儿。"大姑说着匆匆走出屋子。
夜里,躺在硬邦邦的地铺上,我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自行车铃声和远处广播站播放的音乐,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陌生。
我想起小时候大姑家那张木板床,睡着也是硬邦邦的,可那时心里却满是踏实。
"睡不着?"妻子轻声问。
"在想小时候的事。"我翻了个身,"那时候大姑对我特别好,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怕我想家。"
妻子笑了笑:"你大姑是个好人,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特别亲切。"
"那时候大姑和大姑丈日子也不宽裕,表哥还小,家里就那点工资,却从不让我感到委屈。"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大姑半夜三更背着我去医院,第二天天不亮又去上班,那会儿她在县棉纺厂做工,一天三班倒。"
妻子握住我的手:"所以这次咱们一定要好好陪陪大姑。"
第二天一早,我被厨房里的声音吵醒。大姑已经在忙活了,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伴着炒菜的香气飘进客厅。
我悄悄起身,看见大姑正弯腰在灶台前忙碌,苍老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单薄。
"大姑,我来帮忙。"我走过去。
大姑吓了一跳:"怎么起这么早?昨晚睡得好吗?地上硬不硬?"
"睡得挺好的,比我想象的舒服多了。"我笑着接过她手中的铲子,"您歇会儿,让我来炒菜。"
"你会什么啊,城里少爷。"大姑嗔怪道,却也乐呵呵地坐到一旁的小凳子上。
"今天是表哥的婚礼?"我一边翻炒着锅里的青菜,一边问。
"嗯,上午九点开始,在新华饭店,县城最气派的地方。"大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你表哥这次找的媳妇是镇上会计的闺女,模样俊,又有文化,就是家里要的彩礼有点多。"
我注意到大姑说到彩礼时,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很快又舒展开来。
"管他呢,儿子结婚是大事,花点钱值得。"大姑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样干果,"这是我做的零嘴,你最爱吃的,尝尝看还合不合口味。"
我接过来,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蜜饯山楂和糖炒栗子,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满是儿时的味道。
第二天是表哥的婚礼。县城最大的饭店里,摆了八十桌酒席,一眼望不到头。
大厅正中央悬挂着巨大的"囍"字,红色的气球和彩带装点着整个空间,一台老式录音机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和妻子被安排在主桌,表哥西装革履,显得精神抖擞;新娘一袭白纱,头上戴着发箍,看起来很是般配。
婚礼是按照老传统办的,先由媒人致辞,然后新人给长辈敬茶,最后切蛋糕放鞭炮。
大姑站在一旁,穿着她最好的一套深蓝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年轻了十岁。
她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给每张桌子都添茶倒水,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席间,我遇到了小时候的邻居李叔。他还是那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身子骨却依然硬朗。
"小辉啊,在城里混得咋样?"李叔给我倒了杯酒,声音洪亮。
"还行,就是忙,很少回来看看。"我有些惭愧地说。
酒过三巡,李叔悄声告诉我:"你大姑为了这婚事,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女方家要十万块彩礼,你知道你大姑是哪来的钱吗?"
我摇摇头,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把家里那对黄花梨木的箱子卖了,还有你爷爷留下的那块玉佩,都换了钱。"李叔叹了口气,"那箱子可是她奶奶传下来的,一直当宝贝似的供着,谁摸一下都不行。"
我心里一紧。那对黄花梨木箱是大姑成亲时带来的嫁妆,是她最珍视的东西,平时连灰尘都不让落上一点。
爷爷的玉佩更是家族传下来的宝贝,据说是清朝末年的东西,爷爷生前曾说要传给下一代。
"这彩礼钱,你大姑一个人包了大头。"李叔又说,"现在这年头,娶个媳妇不容易哟,没有几万块彩礼,姑娘都不肯嫁。"
我沉默不语,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婚宴上,我注意到表哥媳妇对大姑的态度有些冷淡。大姑端茶送水,新媳妇只是点点头,连句谢谢都没有。
有一次大姑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水,新媳妇皱着眉头说了句:"慢点慢点,别把我的裙子弄湿了。"
语气里带着不耐烦,仿佛大姑不是长辈,而是个做错事的下人。
我有些不舒服,但想到今天是喜日子,也就忍了。
妻子坐在我旁边,捏了捏我的手:"别往心里去,新媳妇可能是紧张。"
席间有人来敬酒,我借机观察大姑丈。他依然沉默寡言,眼神却比以前更加黯淡。
他和大姑的婚姻在当地算是传奇——三十多年前,大姑原本可以嫁给县城一个干部,却因为爱情选择了当时只是个普通工人的大姑丈。
如今大姑丈已经退休在家,每天不是搓麻将就是看电视,很少帮大姑分担家务。
婚宴结束后,我们回到大姑家。大姑忙着收拾东西,妻子主动上前帮忙,两人在厨房里有说有笑。
我趁机去了大姑卧室,想把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刚进门,就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相框,里面是我十岁时的照片,穿着大姑给我买的那件蓝色毛衣,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相框旁边放着一个小布包,我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火车票,仔细一看,全是大姑这些年来看我的车票,从我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张不落地保存着。
我的眼眶湿润了,赶紧把钱塞到枕头底下,悄悄退了出来。
第三天清晨,我起床时发现大姑已经在厨房忙活了。炒鸡蛋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恍惚间,仿佛回到了童年。
"快洗脸,趁热吃,"大姑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铺着一层金黄的鸡蛋,还撒了些葱花,"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记得不?"
我点点头,一口气吃了两大碗。大姑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慈爱。
"吃饱了吗?再来一碗?"大姑问。
"够了够了,再吃就要撑死了。"我笑着推开碗。
大姑收拾碗筷,我帮她把餐桌擦干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大姑花白的头发上,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对了,听说表嫂家条件不错?"我状似随意地问。
大姑点点头:"她爹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家里有些积蓄,人家姑娘又懂事,就是要的彩礼高了点。"
"十万块呢。"我小声嘀咕。
大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谁跟你说的?是不是老李那个大嘴巴?"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钱嘛,花了就花了,儿子娶媳妇是大事。"大姑摆摆手,像是不在意似的,"你表哥这辈子就这一次婚姻,得风风光光的。"
午后,大姑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旧棉袄,递给我:"看看,还认得不?"
我一眼认出那是我小学时穿的,肘部已经磨白了,袖口还有大姑缝补的痕迹。
"你还留着这个?"我有些惊讶。
"舍不得扔,"大姑抚摸着棉袄,"那年你爸下岗,你来我这住,就穿这件。那时你瘦得跟根竹竿似的,看着心疼。"
她顿了顿,眼神变得柔和:"现在好了,自己有出息了,老了也有靠了。"
大姑又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我小时候用过的铅笔盒、课本,还有一张我画的画,歪歪扭扭地写着"大姑好"。
"这些都是你的宝贝,我都给你留着呢。"大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捧在手心,像对待什么稀世珍宝。
晚饭后,表哥和他新婚的妻子来大姑家串门。表嫂穿着一件鲜亮的红色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一看就价值不菲。
"妈,我们明天就搬新家了。"表哥说,"你和爸要不要搬过去住几天?"
我听出表哥的意思是想让大姑去帮忙收拾新房子。
"不用不用,你们小两口自己住。"大姑摆摆手,"妈这几天还要招待你表弟呢。"
表嫂撇撇嘴:"那等你们走了,妈再来帮我们收拾收拾?"
大姑连连点头:"行行行,到时候我去帮忙。"
表哥和表嫂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前表嫂还不忘提醒大姑:"妈,明天早上我们去买窗帘,你要是有空就一起去给参谋参谋。"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有些堵。表哥从小被大姑宠着,如今成家了,想的却只是让大姑去帮忙干活。
"表哥在哪儿工作啊?"我问大姑。
"县里印刷厂,去年刚转正,工资不高,但有个铁饭碗。"大姑脸上带着骄傲,"他媳妇在银行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有五六千呢。"
在县城,这确实算是不错的收入了。我想起大姑为了凑彩礼卖掉的老物件,心里更不是滋味。
第四天晚上,我和妻子收拾行李准备明天返程。
妻子小声告诉我:"我看到大姑的枕头底下压着钱,她一直没动。"
我叹了口气:"大姑这辈子就是这样,给别人的从来不手软,自己的却一分都舍不得花。"
半夜里,迷迷糊糊间我听见客厅有动静,睁眼看到大姑端着一盆热水站在地铺边。
她的动作很轻,生怕吵醒我们:"地上凉,泡泡脚暖和些。"
我假装刚醒:"大姑,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睡?"
大姑有些不好意思:"看你们睡地铺,心里过意不去。这么大人了还睡地上,委屈你们了。"
月光从窗帘缝隙照进来,我看见大姑的眼角有泪光闪动。
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我的被角,确认没有露出来,才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
"大姑,您坐会儿吧。"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大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来。
"睡不着?"她问。
"想起小时候的事了。"我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家里停电,您点着蜡烛陪我做作业,还给我讲故事。"
大姑笑了:"那时候你胆子小,一到晚上就怕黑,非要我陪着。"
"大姑,"我突然问道,"您当年为什么不去省城?"
大姑沉默了一会儿:"当时你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没人照顾。再说了,调到省城有什么用?还不是照样得工作,还要适应新环境。在家乡,好歹有亲戚朋友,日子过得踏实。"
"可您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几分。
"嘘,小声点,别吵醒你媳妇。"大姑拍拍我的肩膀,"生活就这样,没什么好不好的,开心就行。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儿子成家了,你也有出息了,比什么都强。"
她站起身,轻轻擦了擦眼角:"时候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送你们。"
那一刻,许多往事如潮水般涌来。我想起大姑年轻时有机会调到省城工作,却因为要照顾瘫痪的爷爷奶奶而放弃;想起她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总是留给别人,从不计较回报;想起她那双粗糙的手,抚摸过多少人的伤痛与困难。
大姑的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却从不曾抱怨一句。
临行那天,我找了个借口单独和大姑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存折,塞到她手里:"大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大姑丈年纪大了,要多保重身体。"
存折里有两万块钱,是我和妻子商量后又加了些。大姑拿着存折,愣在原地。
"这是干啥?"她有些不知所措,想要推辞。
我握住她的手:"大姑,我记得您说过,世上最宝贵的不是钱,是亲情。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这点钱不算什么,您就收下吧,当是我这个侄子的一点心意。"
大姑的眼圈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傻孩子,"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你自己留着用吧,大姑不缺钱。"
"我知道您不缺,但我想给您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我坚持道,"您这辈子为别人付出太多,也该为自己活活了。"
大姑终于没再推辞,小心翼翼地把存折放进衣兜里:"行,那大姑就收下了。等你下次回来,我做好吃的给你。"
火车缓缓启动,透过车窗,我看见站台上大姑的身影渐渐变小。她一直站在那里,挥舞着手臂,直到看不见为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最深沉的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不是花言巧语的表白,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天;在你迷失的时候,有盏灯为你指引方向;在你成长的路上,有人默默付出,从不求回报。
回城后的第一个月,我给大姑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大姑的声音依然温和:"最近工作忙不忙?吃得好不好?"
我笑着:"都挺好的,大姑,您呢?"
"我能有啥不好的,就是你表嫂怀孕了,每天都要我去帮忙做饭洗衣服。"大姑说着,却听不出半点抱怨,反而充满了期待,"等孩子生下来,我就当太姥姥了,想想就高兴。"
电话那头传来表嫂的声音:"妈,水开了没有?"
大姑匆匆说了句"回头再聊",就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心里五味杂陈。那笔钱,不知道大姑最后有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大姑亲手织的一件毛衣,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孩子,大姑很好,你别惦记。你给的钱,我用来买了台缝纫机,打算给村里孩子们做些衣服。记得常回家看看,大姑等你。"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张照片,是大姑站在她家门口,怀里抱着一台老式缝纫机,笑得像个孩子。
我拿着照片,眼前浮现出大姑在火车站挥手的身影,还有她凌晨三点起来给我端热水时眼角的泪光。
大姑的眼泪,是她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为了家人默默付出,却从不愿让泪水成为别人的负担。
这就是亲情,朴实无华,却胜过世间一切。
我想,来年春天,我还要回去看看大姑,陪她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乘凉,听她讲那些过去的故事,看她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舒展开来,像一本厚重的生活史诗,记录着平凡人生中最不平凡的爱。
文档上传者
热门标签
相关文档
文章说明
本站部分资源搜集整理于互联网或者网友提供,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如果不小心侵犯到你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该资源。